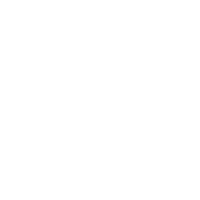
点击数:21 更新时间:2020-05-25

从世界范围看,美国环境法上的公民诉讼(citizensuit)由于其相对完善的法律规定以及深入广泛的法律实践而成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一种典型。公民诉讼(citizensuit)是美国联邦环境法律的一项基本制度,几乎所有重要的联邦环境法律中都包含有公民诉讼条款(citizensuitprovi-sions)[1].公民诉讼是指为保障环境法律的实施,公民、团体依据法律的授权、代表社会公益对违反环境法律的行政机构或私人、组织提起诉讼。其实质是私人实施法律(pri-vateenforcement),即由公民或团体行使由公权力享有的实施法律的权力。作为美国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公民诉讼制度的内容复杂丰富。而有关公民诉讼的限制性因素因其与公民诉讼的一些本位性问题密切相关而成为公民诉讼制度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2].公民诉讼的限制是指公民诉讼的提起及实施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包括立法的限制和司法的限制。立法的限制是指公民诉讼条款中所规定的限制公民诉讼提起及实施的因素。司法的限制是指在公民诉讼的司法实施中,法院运用法律解释机制对公民诉讼所附加的限制。司法限制主要体现为原告起诉资格(stand-ing)问题[3].鉴于国内有关公民诉讼立法限制的研究明显缺失,本文重点考察立法限制问题,研究内容包括公民诉讼提起限制的立法规定、司法实践等,以期更真实地揭示公民诉讼之原貌。
公民诉讼制度一般是通过美国联邦环境法律中的公民诉讼条款体现的。一方面,公民诉讼条款赋予了普通民众提起公民诉讼的广泛的诉权;另一方面,公民诉讼条款对诉讼的提起规定了一定的限制。公民诉讼条款一般规定,公民诉讼必须依法提起,提起公民诉讼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公民诉讼具有明确的可诉范围;但在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下,即使存在符合公民诉讼条款的起诉条件,也不得依据公民诉讼条款提起诉讼。根据公民诉讼条款的规定,提起公民诉讼的限制性因素主要包括三种:公民诉讼具有明确的可诉范围;起诉前必须历经通知(notice)程序;行政机构勤勉地执行法律的行为(diligentprosecution)可以阻止公民诉讼的提起。
一、公民诉讼具有明确的可诉范围
公民诉讼具有明确的可诉范围是指公民诉讼只能针对法律规定的违法情形提起,可诉范围是由法律明确界定的。首先,总体而言,美国联邦环境法律层面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或者普遍意义的公民诉讼条款,提起公民诉讼必须依据各单行联邦环境法律的公民诉讼条款。即,如果某联邦环境法律没有公民诉讼条款的规定,就不存在提起公民诉讼的情形。比如,公民不得依据《联邦杀虫剂、杀真菌剂和灭鼠剂法》(FIFRA)、《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和《海洋哺乳动物法》(MMPA)提起公民诉讼,因为这三部法律没有公民诉讼的规定。其次,就包含公民诉讼条款的各单行联邦环境法律而言,公民诉讼必须依据该法的公民诉讼条款提起。
各单行联邦环境法律的公民诉讼条款一般都规定了明确的可诉范围,包括两类:其一是违反授权该公民诉讼条款的联邦环境法律的特定法律条款或内容的行为,比如违反《清洁水法》(CWA)所规定的排污标准、限制、排污许可证及其条款的行为以及违反行政执法机关依据上述排污标准、限制、排污许可证及其条款所颁布的有关行政规章或命令的行为[4].其二是执行联邦环境法律的联邦环保局等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违法行为。如《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均规定,若联邦环保局局长不能履行本法所规定的不属于环保局局长自由裁量领域的行为或义务,公民可以提起公民诉讼[5].
二、起诉前必须历经通知程序
公民诉讼条款一般规定,原告提起诉讼之前必须经历通知程序,在通知发出之日起一定期限内,不得提起公民诉讼。即,起诉前一定的通知期限可以阻止公民诉讼的提起。通知包括两类:其一,对于违反联邦环境法律特定法律条款或内容的行为,如果有提起公民诉讼之意图,应该在起诉前将被控违法行为以及起诉意图向特定对象发出通知,在通知发出之日起一定期限内,不得起诉。如《清洁水法》规定,原告根据公民诉讼条款的规定,认为存在违反法律所规定的排污标准、限制、许可证及其条款以及执法者根据上述排污标准、限制、许可证及其条款所颁布的行政规章与命令时,如果有起诉的意图,应该将该被控违法行为向环保局局长、被控违法行为发生地所在州政府和违法者发出通知。在通知发出之日起60日内,不得提起公民诉讼[6].其二,对于执法者的不作为违法行为,如果有起诉意图,在将该被控违法行为和起诉意图通知给执法者之日起60日内,不得提起公民诉讼。如《资源保护和再生法》(RCRA)规定,如果原告认为联邦环保局局长不能履行该法所规定的不属于其自由裁量领域的行为或义务,可提起公民诉讼。在起诉前,原告应先将涉嫌违法行为和起诉意图通知给环保局局长,在“原告将其开始诉讼之意图通知给环保局局长之日起60日内,不得提起诉讼。”[7]
关于通知的期限,公民诉讼条款一般规定为60天。但也有一些不同规定,如《资源保护和再生法》规定,针对那些对公众健康或环境带来危险的任何固体或危险废弃物的管理、储藏、处理、运输或清除提供帮助的行为,起诉前通知期限为90天[8].
关于通知的对象,公民诉讼条款一般包括两类:其一,在违反联邦环境法律特定法律条款或内容之情形下,通知对象包括执行联邦环境法律的行政机构、被控违法行为发生地所在州政府和被控违法者。如《清洁水法》规定公民诉讼的通知对象包括:联邦环保局、地区环保局办公室、授权执行水污染防治方案的州政府机构或行政官员和被控违法者……其二,在执法者不作为违法之情形下,通知对象是执法机构的行政首脑。
关于通知的内容,主要包括:被控违反法律的具体行为、被控违法行为违反的具体法律规定、被控应承担法律责任的个人或组织、被控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发出通知的个人或组织的身份证明以及为其服务的律师的姓名、地址等情况{1}.
关于通知的目的,是向违法者和执法者发出警告,以督促其守法或积极实施法律。对于违法者,通知是告知其违法有可能引发公民诉讼,给违法者一个机会对此做出反应并与通知者协商解决争端,以敦促违法者在合理期限内履行守法义务。对于执法者,通知是提醒其存在违法行为,以使其对违法者采取执法措施。此外,也是对执法者发出警告,因为,如果其不采取勤勉的执法行为,则可能导致公民诉讼的提起{1}.
关于通知的效力和功用,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在沃-斯诉废弃物资源公司案(Wallsv.WasteResourcesCorp.,)[10]中判决,通知的要求不是联邦法院可以不予坚持的一项单纯的法律考虑,而是提起公民诉讼的必经程序。即原告必须履行起诉前通知的义务,必须遵循对通知予以规范的公民诉讼条款和行政规章的要求。否则,即使提起公民诉讼,法院也会拒绝对其进行司法审查。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卓姆诉特拉姆克案(Hallstromv.Tillamook)[11]中认为,原告必须履行起诉前的通知程序,因为它可以发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处理环境争议中的作用,以此来避免司法解决。
三、行政机构勤勉地执行法律可以阻止公民诉讼的提起
公民诉讼条款一般规定,对于起诉通知中的违法行为,如果执法者采取勤勉的实施法律之措施,则不得提起公民诉讼。其立法目的在于,国会认为,“公民诉讼旨在联邦政府行为的‘补充’,而非联邦政府行为的阻碍。”{1}即在实施环境法律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公权力。这意味着在公民诉讼提起之前,必须经历行政前置程序;而行政机构勤勉地执法则可以阻止公民诉讼的提起。勤勉的执法具体包括两种情形,即行政机构针对涉嫌违法提起诉讼;行政机构针对涉嫌违法做出民事或行政处罚。
(一)行政机构针对涉嫌违法提起诉讼
公民诉讼条款一般规定,如果执法者针对违法行为,在法院已经或正在勤勉地进行一项旨在要求违法者守法的民事或刑事诉讼,则不得提起公民诉讼。如《清洁水法》的公民诉讼条款规定:“如果环保局局长或州政府在联邦或州的法院已经开始或正在勤勉地进行一项旨在要求违法者遵守有关排污标准、限制或命令的民事或刑事诉讼,……则不得依据该法公民诉讼条款提起公民诉讼。”[12]这意味着,如果行政机构针对涉嫌违法行为提起敦促违法者守法的民事或刑事诉讼,则公民诉讼受到阻止。
不过,对于公民诉讼的这项立法限制,法院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以《清洁水法》的上述规定为例,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司法解释。争议核心问题体现为:何谓“勤勉地执法”?勤勉地执法是否仅限于行政机关在法院所提起的民事或刑事诉讼?是否还应包括行政机关为执法而采取的其他行为?即,能够阻止公民诉讼提起的因素是否仅限于行政机构提起的民事或刑事诉讼,而诸如行政执行命令(administrativecomplianceorder)等非司法性质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公民诉讼的阻止因素。
在公民诉讼的判例中,褒*曼诉**德福特煤炭公司案(Baughmanv.BradfordCoalCo.,)[13]首次声称某些行政行为是属于能够阻止公民诉讼提起的司法行为。该案认为,如果一个行政机构的权力和特性基于其法定的目标使其具有法院的某种性质,并且其执法能力如果同法院实施法律的能力相类似,如都享有对违法行为施加禁止性禁制令(restrictiveinjunction)和民事处罚之权力{2},则该行政行为可视为司法行为,可以阻止公民诉讼的提起。**斯基诉克鲁尼尔沙石公司案(Gardeskiv.ColonialSand&StoneCo.,)[14]认为,“勤勉地执法”应满足三项要求:应该使国会、法院和公众都确信该行政行为是真实的和充分的;该行政行为实施法律之行动是迅速地;要求一项正式的行政程序(主要包括听证、发出公众通知和公众审查等程序){2}
事实上,对于“勤勉地执法”条款,法院大多给予狭义的解释:认为阻止公民诉讼的因素应仅仅局限于行政机构的诉讼行为,并不包括行政执行行为。如地球之友诉统一铁路公司案(FriendsoftheEarthv.ConsolidatedRailCorp.,)[15]和塞拉俱乐部诉切润美国公司案(SierraClubv.ChevronU.S.A.,Inc.,)[16]等著名的案例都表明只有行政机构提起的诉讼才可以阻止公民诉讼的提起{3}.
(二)行政机构针对涉嫌违法做出民事或行政处罚
公民诉讼条款往往规定,行政机构如果针对涉嫌违法行为采取了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也可以阻止公民诉讼的提起。如《濒危物种法》规定,对于违反本法任何条款和依据本法授权颁布的任何规章的行为,如果内政部部长或商业部部长已经依据该法1540(a)条施加了民事处罚,则不得提起公民诉讼[16].
行政机构的民事或行政处罚是否属于阻止公民诉讼的因素,司法实践不尽相同。本文以在公民诉讼限制领域中适用较为深入且极具争议的《清洁水法》第309(g)(6)条为例予以说明。309(g)是《清洁水法》实施(enforcement)条款中的行政处罚(administrativepenalties)的内容,该条规定,执法者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违法者处以两种等级的民事处罚(civilpenalties)。这种以金钱制裁为表现形式的民事处罚本质上属于行政处罚。该条是国会为了增强行政机构实施法律的能力而设计的,这种行政处罚可以阻止以民事处罚为诉讼请求的公民诉讼的提起。309(g)(6)规定,如果执法的联邦或州机构对违法行为施加了以民事处罚为表现形式的行政处罚,公民诉讼不得提起。即:对于违反《清洁水法》的任何行为,如果存在以下三种情形:(1)联邦机构依据本条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勤勉地行为;(2)州机构依据与本条类似的州法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勤勉地行为;(3)联邦或州机构颁发了一项不受进一步的司法审查约束的终局命令或者违法者依据本条或与本条相类似的州法已经支付了所确认的民事处罚。则不得依据《清洁水法》的公民诉讼条款提起以民事处罚为诉讼请求的公民诉讼[17].其立法目的是避免由于执法机构和公民诉讼原告双重实施法律而对同一违法行为重复处罚。
309(g)(6)争议点主要为:其一,何谓阻止公民诉讼的行政行为?阻止公民诉讼提起的是否仅限于民事处罚,是否还包括其他实施法律行为;其二,何谓阻止公民诉讼的诉讼类型?不得提起的公民诉讼是否仅限于以民事处罚为诉讼请求的公民诉讼,是否包括以衡平法上的救济(equitablerelief)为诉讼请求的公民诉讼。法院对此分歧很大,主要采取宽泛解释和狭义解释两种态度。
其一为宽泛解释,认为阻止公民诉讼的实施法律行为并非仅指民事处罚,还包括要求违法者守法的行政执行命令等。宽泛解释之目的是强调行政机关在实施法律方面的主导性,严格限制公民诉讼的提起。典型的案例是南北河流分水岭协会组织诉赛土特镇案(North&SouthRiversWatershedAssn,Inc.v.TownofScituate)[18].赛土特镇经营的一个污水处理厂因无《清洁水法》所要求的NPDES许可证向河流排污,导致马塞诸塞州环境保护部于1987年颁发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其新建废水处理设施和改进现有设施。在赛土特镇履行过程中,环境团体于1989年对其违反《清洁水法》的行为提起公民诉讼,要求民事处罚和衡平法上的救济等诉讼请求。联邦地方法院依据309(g)(6)支持了赛土特镇,认为行政执行命令可以阻止公民诉讼。环境团体在上诉审中主张,能够阻止公民诉讼的只能是行政机构实施的以金钱制裁为表现形式的民事处罚,但第一巡回法院拒绝了其主张,对309(g)(6)做广义的解释,认为只要行政行为已经开始和勤勉地执行,公民诉讼就无提起之必要了[19].
在赛土特镇案中,第一巡回法院是从公民诉讼的目的之角度解释该问题的。法院引用了联邦最高法院在**斯菲尔德沃*尼公司诉**匹克海湾基金会公司案(Gwalt-neyoSmithfield,Ltd.V.ChesapeakeBayFound.,Inc.,)[20]的判决,即,如果把阻止公民诉讼的行政行为仅理解为必须是以金钱制裁为实施形式的话,将从根基处损害公民诉讼的作用—即对政府实施法律的补充作用;将会改变公民诉讼的作用之本质—即从政府实施法律的空隙转至对政府实施法律的侵扰。因为,在联邦最高法院看来,公民诉讼仅仅是政府实施法律行为的补充(supplement)而非代替(supplant)[20].斯密斯菲尔德沃*尼案往往成为联邦法院对公民诉讼进行严格限制的有力武器,“那些同情被告和仇视公民诉讼的法院都通过沃*尼案以支持这种观点:一旦一项行政执行行为已经开始和勤勉地进行,公民就该违法所试图寻求的任何类型的司法救济都应被阻止。”{4}
第一巡回法院不仅把公民诉讼的阻止因素由政府实施的民事处罚行为扩大到行政执行行为,还把公民诉讼的限制类型由原告所提起的以民事处罚为诉讼请求的公民诉讼扩大至以衡平法的救济为诉讼请求的其他公民诉讼形式。第一巡回法院在赛土特镇案中认为,不管是何种形式的救济措施,对一种救济措施所施加的限制,同样也应该适用于其他救济措施。因此,不管是提起以民事处罚为诉讼请求的诉讼,还是以衡平法上的救济为诉讼请求的诉讼,309(g)(6)都可成为公民诉讼的阻止因素{4}.第一巡回法院强调:“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都意识到:(1)实施《清洁水法》的基本责任在于政府;(2)公民诉讼旨在这种基本责任的补充而非代替;(3)只有在政府不能履行该法律责任之际,公民诉讼才是适合的。”{4}
此外,对309(g)(6)做宽泛解释的典型案例还有阿肯色野生生物联盟诉ICI美洲公司案(人rkansasWildlifeFed-erationv.ICIAmericas,Inc)。第八巡回法院遵循了第一巡回法院的判决,声称309(g)(6)(A)的公民诉讼的限制同样适用于以民事处罚和衡平法上的救济为诉讼请求的公民诉讼。
其二为狭义解释,认为应该严格按照国会立法语言进行解释,能够阻止公民诉讼提起的仅限于以金钱制裁为形式的民事处罚,并不包括行政执行命令;主张执法者对违法行为应谨慎地选择实施法律的方式,目的是强调公民诉讼在实施法律方面的积极作用、保障公民诉讼的有效实施。典型的案例是华盛顿公益研究组织诉**勒通毛纺织厂案(WashingtonPub.InterestResearchGroupv.PendletonWoolenMills)[22].**勒通毛纺织厂由于违反了NPDES许可证的排放限制而被联邦环保局颁发了一项行政执行命令,要求其改进设施以遵守NPDES许可证。随后,环境团体提起公民诉讼请求民事处罚等救济。在上诉审中,该工厂主张法院应该超出309(g)(6)之文意,借鉴第一巡回法院在上述赛土特镇案的判决,即行政执行命令和行政处罚都可以阻止公民诉讼的提起。但第九巡回法院拒绝接受,认为309(8)(6)仅限于以民事处罚为表现形式的行政处罚;环保局没有做出行政处罚,而是颁发了行政执行命令,两者是有区别的,因为行政处罚的做出需要公共通知和公众审查等程序,而行政执行命令却无需这些程序{3}.
典型的案例还有西部高品质生活联盟诉纽约市环境保护局案(CoalitionforaLiveableWestSide,Inc.v.NewYorkCityDepartmentofEnvironmentalProtection.)[23]环境团体声称纽约市环保局违反其有关两个污水处理厂的许可,提起以衡平法的救济为请求的公民诉讼,要求纽约市环保局颁发禁止令等。环保局声称应该援引赛土特镇案的判决,依据309(g)(6)(A)对原告所提起的公民诉讼予以阻止。但地方法院认为,该条的阻止因素仅限于以民事处罚为诉讼请求的公民诉讼,该条目的在于确保违反《清洁水法》者不会因同一违法行为而遭致双重民事处罚,虽然法院对于政府行为应给予尊重,但并不能据此而驳回公民诉讼{4}.2005年11月8日,在纸业、联盟工业、化学和能源劳工国际联合会诉**煤炭公司案(Paper,AlliedIndus.,Chem.andEnergyWorkersIntlUnionv.ContlCarbonCo.)[24]中,第十巡回法院拒绝采纳第一、八巡回法院有关严格限制公民诉讼的判决,声称,309(g)(6)(A)有关公民诉讼的阻止因素仅限于原告提起的以民事处罚为诉讼请求的公民诉讼,不包括以衡平法上的救济为诉讼请求的公民诉讼[25].
四、结语
从美国联邦环境法律有关公民诉讼的限制的立法规定及其司法实践来看,公民诉讼的立法限制与公民诉讼的一些本位性问题(如公民诉讼的目的、本质、作用以及司法对美国环境法律实施的影响等)关系密切。
第一,私人实施法律就是公民诉讼的目的及本质。从立法上看,国会在联邦环境法律中设计公民诉讼的目的是明确的,即承认私人在实施环境法律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公民诉讼条款赋予私人行使本应由公权力享有的执法权力,即私人针对法定违法情形可以提起公民诉讼。
第二,公民诉讼的作用就是弥补政府实施法律的不足,为公众实施法律提供机会。一般而言,实施法律的权力主要由公权力行使。但公民诉讼的作用就是当政府不能实施法律(包括政府不作为违法和政府实施法律不力等情况)时,公民诉讼便可以作为“行政机关不作为的消毒剂”(an-tidotetoagencyinaction){2}通过法院来实施法律。公民诉讼的目的是为公众提供更多的进入法院的机会以促进法律的实施{2}.
第三,公民诉讼的作用是有限的。国会虽然充分肯定了公民诉讼在实施环境法律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界定了公民诉讼作用之有限性。因为,国会认为,实施法律的主导性权力由政府享有,公民诉讼只是一种补充{5}.由此可见,在实施法律领域,公权力实施法律机制占据主导地位,公民诉讼的作用只是为了弥补执法机构实施法律的不足。正是基于这种有限性功用的考虑,公民诉讼的立法限制才应运而生。这种制度设计表明只有在行政机构不能有效实施法律之情形下,方可启动公民诉讼。而一旦存在政府有效实施法律之情形,则公民诉讼会受到阻止。这也告诉我们,国会试图在有关公权力实施法律与私人实施法律之间追寻一种内在的平衡之努力。
第四,司法对于公民诉讼限制性因素的解释昭示了美国人看待公民诉讼功效之复杂态度;也彰显了司法对于公民诉讼的深刻影响。争议焦点如下:当一项行政实施行为针对同一涉嫌违法正在进行时,何种执法行为可以阻止公民诉讼的提起;何谓“勤勉的执法”;何谓可以阻止公民诉讼提起的因素;原告可以提起何种诉讼请求形式的公民诉讼等。法院对待这些问题的判决并非一致趋同,而是错综复杂,甚至态度迥异。这也使我们更全面地探究到公民诉讼在美国环境法律的实施等方面所产生的实际效用等。总的来说,公民诉讼的限制性因素经由司法解释而变得弹性十足;公民诉讼的实际功效受到司法自治的巨大影响。当法院意图严格限制公民诉讼的提起、削弱公民诉讼的功效时,往往会对阻止公民诉讼的因素做宽泛解释,倾向于把阻止公民诉讼的行政执法行为做扩大趋势,目的在于强调行政执法的主导地位。而反之,当法院意图重视发挥公民诉讼的积极作用、保障环境法的良好实施时,往往会对阻止公民诉讼的因素做狭义解释,强调严格按照立法规定界定阻止公民诉讼的行政执法行为之范围,目的在于确保公民诉讼的良好实施与有效运转。
总之,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世界典范,美国环境法上的公民诉讼制度在保障环境法的良好实施及公众积极参与环保等方面,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公民诉讼制度体系内对于公民诉讼的限制性因素进行特意的制度设计,也说明:在实施环境法律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行政执法;相对于行政机构实施环境法律机制而言,公民诉讼只是公权力实施法律机制的一种补充。因此,公民诉讼的作用是有限的。此外,有关司法判决也表明公民诉讼的限制还具有其他功效,如减轻司法制度的负担、避免滥诉之可能、节约诉讼成本以及充分发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环境纠纷解决中的重要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