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数:26 更新时间:2025-04-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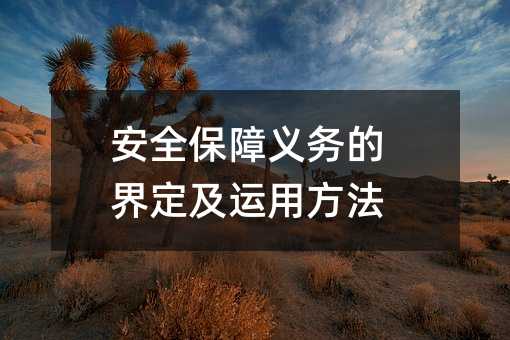
案例二与案例一相比较,均为户外活动,组织者也都理性的判断了存在的风险,都存在因客观原因改变路线等情形,同时路线及交通方式的改变也都经过集体决定,在损害发生后组织者也尽了力所能及的救助义务。但两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差别很大,应该说两案中对活动的营利性判断成为了影响判决结果的重要因素。案例一中法官明确指出“从活动的性质来看,自助式户外运动不具有营利性,组织者并不从中获取利润。因而该类活动的组织者应当承担的责任不同于商业性营利活动的组织者。后者要承担更为严格的责任。”而案例二中法官也认为“综合考虑此类活动的特点,以及王某、曹某组织此类活动有营利的性质,故其应当在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发生的范围内对王某意外所受到的伤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只要组织者从活动中获利就可适用获利规则,这在案例二中也有明确的体现。
有些群众性活动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其组织者也属于专业人士或专业机构,甚至需要对参加者进行相关培训才能开展活动。这些专业性组织者所应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相对于普通组织者而言,显然应当要求更高、范围更广。这一规则的理论基础首先为危险控制理论,控制危险最便利最积极有效的主体就是安全保障义务的义务主体。没有人比这些专业性组织者更能积极有效的控制风险,而由他们控制风险也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约社会成本。其次,是信赖关系理论,对于参加者而言参加专业性组织者组织的具有专业性的活动对其组织者的信赖程度比参加一般性质的活动要更高。其信赖专业性组织者的职业水准,而专业性组织者也应当满足这种信赖。故,作为专业性组织者在组织具有专业性质的活动时应承担较普通组织者更广泛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成为一种合理的区分标准。
某公司于2009年6月13日举办“双龙罗布泊冠军版豪情越野挑战赛”活动。李某报名,并与某公司签订《安全协议书》,李某未接受培训。李某乘坐同为试驾人员的王某驾驶的汽车发生事故,受伤。交通管理部门认定王明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遂起诉王明、某公司要求赔偿。法院支持了李某的诉讼请求。
在案例三中,某公司是专业的汽车销售公司,举办的越野挑战赛有明显的专业汽车运动性质。尽管该公司与李耕签订了《安全协议书》,而协议书中也没有约定该公司所应履行的义务及应承担的责任。但,法官认为“试驾车辆在人工设置的越野赛道上进行,存在一定风险,某公司应当对参加活动的人员进行相关的安全培训。……但李某未能接受到相关培训。……某公司认可王某是无权带领他人参赛的,而某公司又未提供证据证明李某、和王某是未经允许私自试驾,因此该公司存在错误。”分析案例三,可以发现李某是成年人,具有一定的风险判断能力,但汽车越野赛是一种专业性活动,普通人对于其风险的判断是感性的、有限的。这就要求专业组织者提供更为完善的安全保障而绝非告知风险即可免责。本案中法官并不认定李某存在过错,而在没有具体法律规定、行业标准或约定义务的情况下,认定某公司没有履行安全培训、严格控制私自驾驶等安全保障义务,这种判断就体现了对于专业性组织者组织专业活动应承担更为广泛和严格的安全保障义务的价值取向。
诚实信用原则是安全保障义务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甚至可以说催生了这一制度的产生。德国法上的一般安全注意义务就是由诚实信用原则扩张衍生而来。诚实信用原则具有很强的扩张功能,即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在于赋予法官在具体案件中按正义的要求扩张当事人的义务之自由裁量权,而这些义务正是制定法所未事先规定的。在此提出这一原则,是因为群众性活动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活动领域,在处理一些新型或具有特殊性的活动时,如果现有原则、规则无法满足保证公平正义的需要时,就需要法官发挥自由裁量权,运用诚实信用原则保证案件的公正处理。
案例四:李某、王某、卢某与苏某、柳州市第二中学、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柳州中心支公司旅游合同纠纷案
2009年,柳州二中组织教师到石门冲景区进行旅游。景区的经营者为苏某。卢某酒后在景区游泳池游泳身亡。卢某之亲属起诉苏某赔偿,柳州二中、保险公司作为第三人应诉。法院认定卢某应承担主要责任比例为60%;苏某虽履行了警示义务,但安保义务存在瑕疵,应承担30%责任,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责任;柳州二中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对参加者未尽安全监管义务,承担10%的责任,但经法院释明,因李某、王某、卢某某表示不起诉柳州二中,法院未予判决。
群众性活动往往需要在一定的场所进行,而这些场所大多是公共场所。在活动中组织者与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同时承担着安全保障义务,两者之间既有重合也有区别。当损害结果发生,二者发生竞合时,对其进行区分并分别认定责任就是这类案件的难点。
安全保障义务从内容上主要包括预防风险、排除风险和救助义务。在群众性活动中,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侧重于组织工作,包括活动的时间、地点的策划,对交通的安排,在活动期间对参加者的监管、救助等。而公共场所作为活动地点,其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则主要侧重于与活动场地有关的风险的控制,当然在发生危险后,也负有排除危险和救助的义务。由此可以看出,安全保障义务都是围绕着组织者和管理人这两个核心的行为的不同侧重点在向外扩展,与一方关系更近的安全保障义务就应该被视为属于这一方的义务范围。笔者将其归纳为“重心规则”。其理论基础为危险控制理论,组织者的组织行为所能控制的风险与管理人的管理行为能控制的风险显然有区分,所以二者所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也因此而不同。
从案例四中可以看出,法官首先认定了受害人自己在判断风险上的过错以及应当承担的责任。而后对景区管理人和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范围做了区分。景区管理人在泳池布置了警示标志,履行了警示义务,但是没有配置保安阻止饮酒后的游泳者进入泳池,也没有配置救生员保障游泳者的安全,并实施救助。因此,景区管理人没有全面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作为活动组织者,对于参加者负有安全监管的义务,尤其对于饮酒后的人员更应该使其避免参加有危险性的活动,柳州二中并未履行这一义务,因此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本案中虽然组织者和管理人都负有救助义务,但是在游泳池发生危险,泳池管理人的救助义务更大,更合理,因此不能将专业救护的责任加在组织者一方。
在原告没有起诉组织者的情况下,法院应依职权追加其为第三人。在确定组织者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并应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应向原告行使释明权。如原告申请追加组织者为被告,应予准许,如原告坚持对组织者不予起诉,则法官依然应在判决中分清责任,记录裁判过程。在原告没有起诉管理人的情况下同样适用上述审理方式。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也发现很多类似案件,在原告不追究组织者责任的情况下,有些法官并没有追加组织者为第三人;没有明确组织者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承担责任;也没有向原告行使释明权。这样做首先可能使原告由于法律知识的欠缺,没有认识到组织者的责任而无法保护自己的权益;也有可能使活动场所的管理人实际承担了或误以为自己承担了过多的安全保障义务。笔者认为,案例四中法官的审判方式是正确的,在类似案件中应予以注意,以达到司法标准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