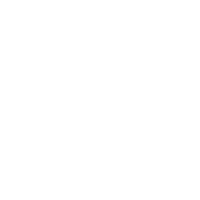
点击数:31 更新时间:2024-07-16

对于犯罪记录封存效力存在分歧的原因可归结为两点。首先,在刑事诉讼法规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保密的同时,司法机关和其他单位被赋予了查询权。其次,在犯罪量刑中,符合封存规定的部分犯罪可能会影响累犯或再犯的成立,具有实体法上的效力。
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未成年人的普通犯罪无论刑罚和刑期,都不构成累犯。然而,如果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或者毒品犯罪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封存犯罪记录。但是根据刑法第六十六条和三百五十六条之规定,如果行为人再犯一定之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毒品犯罪的),可能构成特殊累犯或者毒品犯罪再犯,应当从重处罚。认定特殊累犯和毒品犯罪再犯意味着对前罪的再次评价,而一旦评价,则意味着案件记录未实现保密。查询权和刑法的相关规定导致了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与刑罚裁量的冲突。
如何保持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所带来的刑事诉讼法的程序效力和刑法的实体效力的一致性,是未成年人案件记录封存制度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一冲突的解决不能简单依赖于法律条文的文义解释,需要进行立法初衷的目的解释。刑事诉讼法规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初衷在于,社会原因和家庭原因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鉴于未成年人的社会认知能力有限且其矫正可塑性较大,为淡化“犯罪标签”对其成长的影响,因而保障未成年人的个人权利,以便其更好地回归社会。刑法之所以在特殊累犯和再犯从重处罚的规定中未排除未成年人,根本原因在于特定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突出,且未成年人参与犯罪的数量较大,为了更好地威慑犯罪和预防犯罪。
可见,刑事诉讼法和刑法规定的效力冲突实则个人权利保障和社会秩序维护的冲突。个人权利和社会秩序的冲突和协调可谓法律的永恒课题,协调这一冲突并无放之四海的统一标准,其随着社会发展需要而不断调试。从我国特定犯罪和未成年人的犯罪现状出发,纵然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具有重大意义,但是一味地封存意味着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放纵,不仅无法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护,也无法实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也正因如此,我国并未选择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而选择了犯罪记录的封存制度。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所带来的个人权利和社会秩序的冲突,我国不能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应当实现同时兼顾。换言之,既需要关注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障,也需要关注刑法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为实现这一目的,现有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刑法有关特殊累犯和毒品犯罪再犯的规定都应当做出妥协。对此,未成年人的普通犯罪应当绝对封存,但是未成年人的特殊犯罪记录——符合特殊累犯的犯罪和特定的毒品犯罪的犯罪记录——应当设定一定的封存考验期。以所判刑期为考验期,在考验期内,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相对封存:如果在考验期内,行为人再次故意犯一定之罪的,可以根据原所犯之罪认定特殊累犯或者毒品再犯;在考验期内未再次故意犯一定之罪的,考验期满,相关犯罪应当绝对封存,原所犯之罪不能再作为特殊累犯或者毒品犯罪再犯的认定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