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数:44 更新时间:2025-0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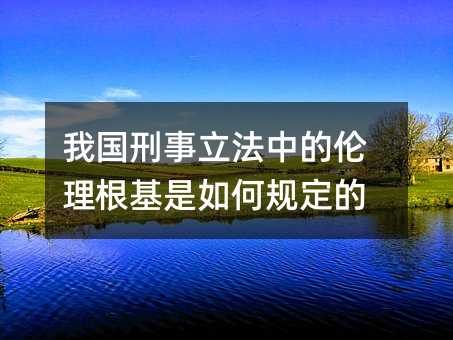
刑法一般来说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而伦理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尽管刑罚与伦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们都属于社会上层建筑,都是被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同时,道德与法律共同执行着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能,因此刑法的适用不能完全脱离伦理的因素。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根据伦理的观点,行为可以分为无意识行为和有意识行为。无意识行为是指不由道德意识引起,也不涉及自觉有益或有害社会和他人的行为,刑法不予调整。有意识行为是指刑事立法上所规定的危害行为,伦理上认为这是有利或有害于社会和他人的行为,犯罪是道德行为或伦理行为的一种类型。
犯罪行为的伦理性成为规定危害行为为犯罪行为的根基。伦理行为的基本特征是个人基于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自觉态度而自主选择的结果,而犯罪是反映人的主体性、危害社会的行为。因此,从伦理行为类型归属上看,犯罪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或叫伦理上的非行。
刑罚是国家创制的,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犯罪人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其某种权益的强制性制裁方法。刑罚体现了国家对犯罪人及其行为的否定性评价,旨在教育全社会所有的公民,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公民的安宁。刑罚具有道义谴责性,是具有内在道义根据的价值判断,也与社会道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刑罚的伦理根基主要在于其对犯罪行为的报应。刑罚必须具有对恶行予以恶报的属性,超过犯罪份量的不具有平等性的刑罚是非正义的刑罚,也是不人道的刑罚。刑罚是因为犯罪而加于罪犯的国家的非难形式,具有非难的意义,是一种恶害痛苦的程度与犯罪相适应的恶。刑罚必须有其伦理根基,因此在立法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道德和伦理的评价,力求达到伦理与法律的一致。
近代以来,在探索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刑法的移植成为主要途径。然而,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道德根基,被移植的法律制度与观念无法获得本地沃土与持续成长的养分,导致刑法无法有效成长。在我国刑法中,部分内容脱离了道德要求,导致法律无法取得预期的结果。
法律应当与人情相合,法律与道德应该是一致的。如果法律与道德相违背,就需要反思法律规定的妥当性。在我国刑事立法中,有些条款的设立不符合这一理念。例如,将亲属之间的隐匿行为入罪化,严厉处罚近亲属,与社会伦理道德要求相背离,导致罪刑不均衡。
刑罚种类及适用应体现人道、合理、公平性,但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存在伦理缺失。监禁刑的执行会影响罪犯的社会化,使罪犯丧失了社会化的基本条件和环境,导致刑罚的社会化效果不佳。同时,我国刑罚结构趋重,罪刑之间不平衡,非监禁刑的适用不足。
国家的法律应该符合人之常情、常理,与社会伦理性因素相吻合,使法律得到普遍、有效的执行。在创制新的刑事法规、规定新罪名时,立法者应保持谦抑的态度,吸收社会伦理性因素,使刑法得到有效实施。在设置法定刑时,应照顾到伦理性的特殊要素,体现罪刑均衡,从而有助于实现刑罚适用的公平性。
对于亲属之间隐匿行为入罪化,应考虑我国社会伦理道德要求,减轻近亲属的处罚。因此,应对现行法律作出修改,免除或减轻近亲属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隐匿行为的处罚。
刑罚种类的构建应体现人道、合理、公平性。应大力推行非监禁刑的适用,减少刑罚适用的社会成本,提高刑罚适用的效益。在刑罚结构中应增加非监禁刑的种类,以减少刑罚的重压,实现刑罚适用的公平性。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利用各种职业权利或营业实施犯罪的现象日益突出。例如,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罪”中的故意泄露商业秘密、证券交易中非法操纵和内幕交易、制造销售伪劣产品、利用计算机犯罪等犯罪行为。这些犯罪人都是利用其职业上的便利而实施的。
对于这些犯罪人,运用自由刑去制裁未必必要,因为从剥夺自由的必要性角度来看,可能并不需要剥夺其自由。然而,自由刑的弊端可能给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带来困难。罚金的制裁方式无法有效地剥夺或限制其利用职务继续犯罪的条件。剥夺政治权利的方式则可能剥夺了一些无需剥夺的权利,而没有剥夺真正应该剥夺的权利。只有剥夺犯罪人从事特定职业的资格,才能在遏制犯罪人再犯同类罪方面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在犯罪人拥有人身自由但缺乏特定资格的条件下,其犯罪能力将受到极大的限制。犯罪人想要再度借职务之便,首先就会在资格方面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将“禁止从事一定的职业”增加为资格刑的一种形式,不仅可以充分发挥资格刑在惩治职务犯罪方面的作用,满足刑罚谦抑性和经济性等现代刑事政策的要求,还能获得社会大众的情感认同,增强其伦理根基。
现行刑法典第39条规定了被判处管制刑的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应当遵守的若干规定。然而,与其他国家类似的刑罚制度相比,我国刑法对管制刑的具体惩罚内容或监督内容还是较少。刑罚的强度不够,执行内容较为虚泛,缺乏刑罚的可感性,难以对罪犯形成应有的心理强制与外在压力,导致该刑种的惩戒作用十分有限。
为了提高管制刑的适用效率,完善管制的行刑内容并适度加大刑法强度是十分必要的。结合我国国情,可以在管制刑的行刑内容中引入社区劳动制度。根据情况对被判处管制的罪犯附加判处一定时间或数量的社区公益劳动。这样既可以体现对犯罪的惩罚,又可以通过行刑矫正罪犯,使受害者以及社会得到实实在在的补偿。
犯罪是一种恶,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刑法也是一种恶,一种不得已的恶。因此,刑法的内容及其实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限制因素之一是社会伦理的制约。从犯罪、刑罚与社会伦理的关系可知,刑法具有伦理性根基。因此,在刑事立法的过程中,应该吸收伦理因素,使制订出来的法律符合大众情感,顺应民意。同时,也要注意其理性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使刑法获得大众认同,使之成为一部体现正义的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