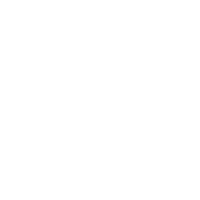
点击数:48 更新时间:2024-12-07

近年来,中国社会围绕“大义灭亲”和“亲亲相隐”两种立场展开激烈的博弈,亲属豁免权的诉求逐渐增长。亲属豁免权的立法首先在刑事诉讼的作证领域开启,但由于部门利益之间的博弈,该制度的初衷未能实现。传统文化的复兴为“亲亲相隐”的回归提供了合理性和动力之源,但传统思维方式为亲属作证豁免权设置了障碍。来自文化的力量使该权利具有了中国独特的面貌。因此,亲属豁免权在中国应该循序渐进、有限推进、不断完善、成熟推广。
中国是一个宗法伦理社会,亲情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因此,国家将维护亲情视为法律保护的更高价值。在中国,“亲亲相隐”一直以官方话语的形式存在。一方面,统治者倡导亲属之间的相互隐瞒;另一方面,国家将“亲亲相隐”视为民众的义务。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亲亲相隐”制度被废除。这种话语的中断不仅是新政权与旧制度决裂的需要,更有深层次的原因。革命主义的“斗争哲学”和“人性观”导致家庭和亲情观念受到批判,官方话语地位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大义灭亲”式的话语表达。
在当代中国,虽然阶级学说和斗争哲学的影响逐渐减弱,法律也在渐进地去政治化,但“大义灭亲”式的法制模式仍然存在于中国法律制度中。随着社会解构和人性观念的回归,人权和法治意识逐渐提升,对“大义灭亲”法制模式的质疑和批判逐渐增强,对亲属作证豁免权的诉求逐渐增长。民间话语的壮大构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亲属豁免权正在萌发和涌动。然而,该权利目前还不能从根本上颠覆“大义灭亲”的法制模式,因为该模式为国家和部门利益带来了好处,立法者不愿也不能完全抛弃这一传统。但民间话语的成长和壮大对官方构成了一定压力。为了满足民众需求,传统法制模式必须突破,立法者选择在亲属作证领域开启亲属豁免权。然而,面对坚固的传统,立法者不敢跑得太远,同时也要兼顾其他部门的利益。因此,亲属作证豁免权在中国具有独特的面貌。
中国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然而,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亲属豁免权。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实际上是对亲属作证豁免权的一种“打折”处理,这是因为公安和检察机关的抵触。这种“打折式”立法反映了立法者在权力博弈中的纠结和无奈。公众对“大义灭亲”式法制模式的反感,促使立法者突破传统的“所有人都有作证义务”模式。然而,面对强势部门的压力,尤其是在强势部门施压下,立法者不得不考虑它们的意见。因此,在绕过公安和检察机关的情况下,亲属作证豁免权在刑事诉讼领域出现。在刑事审判模式下,证人出庭并不是必须的,甚至在既有诉讼结构下,证人出庭通常也不会改变法官的“内心确信”。当由公安、检察和法院共同构建的堡垒趋向坚不可摧时,证人出庭的价值就被消解了。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的只是“不强迫到庭”,并不意味着可以拒绝作证,如果法院认为有必要,仍然可以要求亲属在庭审中作证。这样,法院的利益并未受损,反而增加了灵活性。因此,法院对这一规定并没有像公安和检察机关那样表现出明显的抵触。
“亲亲相隐”思潮的兴起既有现实需求,又有文化动因。近年来,传统文化的复兴推动了这种思潮和话语的发展。传统中国的法治资源有限,因此进行了法制现代化运动。然而,现代中国的法律和法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模仿西方建立的。面对以西方话语为主导的中国法制现代化,国人心中存在一种“不得不”的痛苦和“欲迎还拒”的心态。容隐制度并非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有产物,而是跨越时空的普遍现象。因此,无论是将亲属包庇伪证的除罪化工程视为“继承传统”还是“移植外法”,都是无关紧要的。然而,中国学者在阐释这一问题时,更倾向于“继承”这一表述,或者先表述为“继承”,然后再表述为“移植”。传统文化的复兴得到了官方的鼓励和支持,也被视为实现文化自觉、自信和自强的必要途径。因此,以“亲亲相隐”传统话语的方式表述亲属豁免权既满足了国人的文化虚荣心,也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需求,降低了民众和政府的拒斥程度,提高了可接受性和政治安全性。
然而,传统文化不仅带来动力,也带来阻力。尽管现代革命的“斗争哲学”和“人性观”在“大义灭亲”法制模式的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但传统的“结果主义”思维对其影响也不能忽视。这种思维在司法上表现为:司法的目的是正确裁判,正确裁判的关键在于发现真相。因此,只要能发现事实,可以使用任何手段,不排斥任何技术。在中国古代司法中,“诈供”、“骗供”、“诱供”屡见不鲜,刑讯逼供司空见惯,并被宣扬为“妙判”的技巧。这种思维仍然存在于现代司法中。在这种思维下,法律事实与客观真相、法律内正义与法律外正义混淆,司法的“过程性”和“形式性”价值受到排斥,而发现真相成为审判的终极目标。在这种思维下,在司法过程中,亲属提供的证据,特别是不利于当事人的证据,不受限制,相反,亲属提供线索或配合成为侦查机关破案的常用手段。因此,传统文化既带来了亲属豁免权的动力,也为不合规运作提供了理由,为亲属作证豁免权设置了障碍,使该制度的初衷无法实现。
亲属豁免权在中国刑事诉讼领域的尝试受到“目的转换”的命运,该制度的初衷几乎消耗殆尽。然而,我们仍然要理性看待这一现象。新刑诉法对亲属作证豁免权的规定至少表明立法者开始关注亲属关系在司法中的特殊性问题,开始意识到在司法中除了发现犯罪事实外还有其他价值需要保护。这些关注和意识是当代中国权利观念和法治意识发展的产物。社会发展需要通过试错来逐步推进。因此,亲属作证豁免权的尝试虽然不成功,但仍然具有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法律发展国家来说,在复杂的利益格局中,试错是不可避免的。
在传统中国,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在道德上并不冲突,因为中国古人将它们放在不同的领域针对不同的主体提倡。我们反对的是“大义灭亲”在私人领域出于促进司法效率的考虑而强制公民作证。因此,亲属豁免权可以在普通人之间行使,但在涉及执法或司法的国家公职人员时应受到限制。鉴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在亲属豁免权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上,可以先在民事诉讼领域进行尝试,为刑事领域的豁免权积累经验,待经验成熟后再在刑事诉讼领域全面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