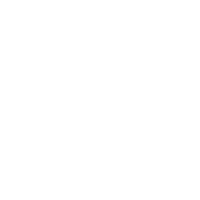
点击数:19 更新时间:2024-05-21

【出处】中国诉讼法律网
【摘要】司法调解的契约化是私法领域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司法调解处于合同领域和诉讼领域的交汇处,所以它的契约化是当前我国私法领域中强调合同自由和诉讼当事人主义的必然发展趋势。司法调解的契约化发展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司法调解原则金字塔式结构体系的形成,自愿原则处于金字塔之顶端,保密、对等、诚信三项原则的共同运作以保障自愿原则的实现;二是司法调解中主持人的多元化引起法官角色的重整,以保障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意愿自由交换。
【关键词】司法调解;契约化;ADR诚信
【写作年份】2011年
【正文】
替代诉讼纠纷解决方式(ADR)运动所带来的“非讼化”趋向正逐渐改变着诉讼的原有结构;“诉讼契约化”成为这一改变的集中体现。国内已有学者对这种新的改变做了相关阐述。[1]民事诉讼的契约化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在民事诉讼领域的体现”;[2]它意味着“从当事人自治、意识自由、当事人的自主性角度系统地按照契约化的思路对民事诉讼体制进行修正,使其满足社会转型的需要”。[3]其中,诉讼和解或诉讼调解,[4]即在诉讼进行中,当事人就解决该诉讼实体争议达成的合意,自然也是诉讼契约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诉讼契约化”在西方国家的出现实际上是对于民事诉讼原始契约本质的回归。20世纪在法国诉讼法学家之间展开的关于诉讼契约本质的争论中,赞同者强调民事诉讼和合同之间的相似性,比如,诉讼的封闭性和合同的不可触犯性,判决的既判力和合同约定的相对效力,甚至也有学者将诉讼的应诉等同于合同中的承诺。不过,这番争论以诉讼关系的法定性质结束,否认了诉讼的契约性质。1975年新《民事诉讼法》的出台最终确定了诉讼和合同的分离。[5]诉讼和合同成为两个相对立的概念:前者意味着当事人意愿的分歧,后者意味着当事人意愿的趋同。[6]然而,近年来“诉讼契约化”和“契约诉讼化”共同诠释的“契约正义(或司法)”理念蕴含着诉讼和合同的再联合。[7]
在中国,一直以来,民事诉讼的改革都在努力摆脱原有职权主义模式的影响,强化当事人诉讼主体的积极地位,从而实现当事人主义模式的结构。“诉讼契约化”正是模式转换的一个总结;这对于我国的民事诉讼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方向,并非一种回归。同样,“契约化”对于我国的司法调解(或称“法院调解”、“诉讼调解”)也是一个全新的方向。从建国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8]到建国后的“调解型审判方式”,[9]调解在民事程序中长期以来被视为与判决相平行的一种审判方式。调解和诉讼程序不严格区分:启动调解程序的随意性很大,法官可随时随地将纠纷从诉讼程序转入调解程序,以逃脱诉讼程序刚性带来的约束;[10]而在调解程序中,法官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依赖于调解的合法和真实原则,[11]他恣意约束当事人意愿的效力,以自己的判决方案取代当事人的合意。这样的程序结构模式造成一种“畸形”的产物:“调解式判决”,即带有“调解”的名义或特征,但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实际上为法官一方意思表示的裁决结果。[12]
司法调解的改革旨在“纯化”当事人的合意和弱化调解中的职权主义特征。[13]从最初的“调解为主,审判为辅”,到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的“着重调解”,[14]再到1991年《民事诉讼法》的“自愿和合法调解”。调解在民事诉讼立法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然而,实践中民商事一审案件的调解率在20世纪90年代仍然保持在50%左右。这是因为,调解在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充当着一个磨合立法与实践的调制器,弥合法律职业化之前的活动空缺,甚至也在帮助法官减少职业所带来的风险。 [page]
从20世纪末,民事程序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关于民事诉讼模式,从职权主义到当事人主义模式的转变获得相当的成果。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肖扬在2007年1月5日的第七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指出:“合乎国情的民事诉讼模式已经基本形成。”虽然从2001年开始,民商事一审案件的判决率超过调解率,但是,外部环境的改良,ADR运动蕴含的非讼化理念提供了调解新的发展空间,调解作为多元化诉讼或司法的一部分被保留和发展。
新世纪的司法调解是在法律、司法、诉讼这些大“背景”变革之下的创造性发展。总方向是继续延伸以往的思路,即纯化当事人合意和弱化法官职权干预;简而言之,我们将之总结为司法调解的“契约化”。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颁布是司法调解“契约化”的一个重要“界碑”。《规定》重新构造了司法调解的原则:自愿原则的提升、保密原则的有限建立、抛弃真实原则、限制合法原则。[15]然而,司法调解契约化的进程任重而道远,如何确保当事人合意,确切地说当事人“真实”合意的实现,是现代调解“正义”实现的关键。
根据我们强调欲恢复的调解的契约本质,调解自愿或自由,如合同自由,作为意思自治原则在调解领域中的体现,将是调解改革的最终目的。然而,合同领域中契约自由的演变和发展表明,现实中当事人自然力量的不对等,特别是消费社会中商家对于消费者的强大,造成当事人自由交换的信息和机会不均等;于是,司法的适度介入被期盼为矫正天平失衡的手段。在法国私法领域中,合同的“道德化”、社会化、诉讼化成为实现契约正义的新手段。同样,在法国民事诉讼的特定背景下,法国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义模式逐渐容许法官的积极介入,以平衡当事人的力量对比和控制当事人绝对主导诉讼进程造成的拖延现象。结合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因素的“混合型”诉讼模式成为新的实现程序正义的方式。
我们认为,调解在混合型模式中将起关键的“调制器”作用,以平衡当事人主义因素和职权主义因素。在狭义的诉讼范围内,法官能动性的扩充助长了职权主义因素的增加。但是,当事人的主动性,或当事人主义因素,在诉讼范围之外依赖调解得到扩充。当事人可以通过选择来摆脱法官能动性的控制,因为后者限于审判职能的行使。在民事程序这个范畴内两种模式的交汇得到一种平衡。对于我国的司法调解,则必须要纯化当事人的合意,因为如果不能实现这点,那么所谓“协同型”或者“和谐型”模式将只是职权主义的回归。
在司法调解之内也包含着当事人主义因素和职权主义因素的竞争,换言之,即当事人意愿和法官能动性的竞争。司法调解介于合同和诉讼两大领域之间。相比纯粹的合同领域,法官在调解中的能动性可能表现为调解协议形成前阶段的介入,而不局限于协议形成后阶段的介入。相比纯粹的诉讼领域,法官的能动性难以触及调解协议实质性内容的形成,大部分局限于程序的介入。司法调解契约化旨在追求当事人合意的真实化,而“真实”合意的实现期待于法官的适当能动性保障当事人在调解中的意愿自由。一方面,司法调解的原则继续重塑的进程,形成金字塔结构式的原则体系。自愿原则居于金字塔之首,保密、对等、诚信三项基本原则的共同运作,以贯彻自愿原则的实现。另一方面,法官在司法调解中的角色实现重整,既要保障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意愿自由交换,又要防止自身形成对当事人意愿的干涉。
一、司法调解原则的重塑
自愿原则是司法调解的一项基本原则。学者们认为该原则应当包括程序上的自愿和实体上的自愿两层含义,前者是指“当事人主动向人民法院申请用调解方式解决他们的纠纷,或者同意人民法院为他们做调解工作解决纠纷”;后者是指“当事人双方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是互谅互让,自愿协商的结果”。[16]然而自愿原则在实践中的贯彻存在严重问题。《规定》虽然加强了合意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力,[17]但是关于合意对法官的约束力存在欠缺。《规定》第12条对调解协议无效的条件予以界定: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侵害案外人利益;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但是,如何判断违反当事人“真实意思”,自愿原则很难提供具体的衡量标准,实践中也就无法避免法官可能滥用自由裁量权过宽地涉入调解协议的审查。自愿原则的具体化落实,应当体现在调解程序的始终,以及调解协议的内容和形式。自愿原则的实现不是孤立的,必须依赖于配套的一系列原则。因此,关于司法调解的原则,我们可以构建一个金字塔结构式的体系:自愿原则处于金字塔之首,统治着下属的次要原则——保密、对等、诚信原则;而这些次要原则的共同实施保障着自愿原则的真正贯彻落实。总而言之,自愿的调解既是保密的调解,也是对等的调解。 [page]
(一)调解的保密性
《规定》第7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申请不公开进行调解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该条款被视为确立调解保密原则的标志。然而,比较国际调解规则[18]和外国法律中关于调解保密原则的规定,[19]《规定》的阐释就显得非常狭窄。照搬“诉讼不公开”制度,司法调解的保密限于“程序的封闭形式”,即调解程序不公开进行,禁止与诉讼无关的第三人的参与和旁听。这种狭隘的诠释缺失调解保密原则的核心内容,即“调解信息保密”。虽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但是这项条款对调解信息的保护,仅限于当事人作出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并且,保护的手段也仅限于“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在调解程序结束后,法官和当事人依然享有很大的空间将自己在调解中知悉的信息使用到之后的诉讼程序中。在2007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中,虽然强调“办案法官和参与调解的有关组织以及其他个人,应当严格保守调解信息,当事人要求不公开调解协议内容的,人民法院应当允许”,但是对于调解信息是否允许在之后的程序中使用,仍然未给出答案。另外,即使就调解程序的“不公开进行”而言,它的启动也需要当事人提出申请。在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情况下,调解似乎应该是公开进行的。如此,司法调解适用的是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
司法调解的改革逐渐实现调解和审判程序的相对分离,法官“一身兼两职”的角色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然而,即使在“调审分离”的状态下,由于缺失调解信息的保密义务,调解信息仍然有可能跨越调解和审判程序的隔阂,进入审判程序;审判法官即使没有介入调解程序,仍然可能受到调解信息的影响,或者进而依据这些信息做出判决。如此,我们试图通过“调审分离”实现当事人合意“纯化”的努力将付诸东流。同时,调审的相对分离仍然保留着部分“调审合一”的状态。在“调审合一”的结构中,审判法官同时也是调解法官,调解信息保密义务的缺失使得当事人“合意”随时有被法官“恣意”取代的危险。调解保密原则的确立因此被视为维护调解中当事人意愿自由的首要手段。然而,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维护调解程序的安定性,而且在于保障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因为缺失保密原则的保护,当事人将会害怕自己的“坦诚相对”成为之后诉讼中针对自己的不利证据。于是,他们不敢随意披露自己的观点,展示自己拥有的证据,做出任何承认和承诺,对待对方提出的方案也会慎之又慎。在缺失当事人真实自由意愿的情形下,调解程序的进展举步维艰。同时,允许调解信息的泄露,可能使部分真实性带有折扣的证据材料进入审判程序,从而成为不公正判决的基础。
调解信息的保密范畴采取分级制,划分为初级保密范畴和高级保密范畴。一般而言,所有“与调解有关的信息”都属于初级保密的范畴,它们被禁止随意披露。关于“与调解有关的信息”的定义,我们借鉴《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调解示范法》颁布指南中的定义,即包括调解程序中披露的信息,调解程序的进展和结果,在调解协议达成前所有有关调解的信息。例如,关于调解可能性的讨论、调解条款、调解员的选择、关于调解的邀请和接受或拒绝等。不过,在司法调解中,这些信息中的一部分将被允许在任何情形下被披露,例如,关于调解的存在和结果的信息。因为司法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比诉讼外调解协议更强的法律效力,即强制执行的效力,这可能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并且调解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中成为“司法调解”,就会受到诉讼的司法属性的影响,自然也包括有限制地遵守公开原则。在案件以调解协议结案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这种结果行为应让公众知道,然而,关于调解协议的内容,则不予披露。不过,在调解协议的执行中,如果涉及第三人的利益,第三人将有权利知悉调解协议的内容中有关其利益的部分。 [page]
在调解以失败结束后,纠纷进入诉讼程序中,这些不予披露的“与调解有关的信息”将实行再次的分类:一部分调解信息将从“初级保密”范畴划分出来纳入“高级保密”范畴;高级保密范畴内的信息将继续被禁止在诉讼程序中予以披露,而剩余的初级保密信息将被允许披露。调解信息的保密分级旨在调和调解程序安定性和诉讼程序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禁止披露所有的调解信息,调解程序将有可能被某些的当事人利用。例如,对方出于对调解程序的信任出示了很多其拥有的证据,调解失败进入诉讼程序,这些证据如果依据保密原则全部被禁止出示于诉讼程序中,显然,“诚实”的一方将会失去其证据优势,“狡猾”的一方就会理所当然地获得证据优势。因此,为了避免“陷阱”的设置,调解信息的保密级别划分就成为关键。
那么,哪些信息属于“高级保密”范畴呢?我们试图对调解信息在借鉴于“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的区分上予以划分。法律事实是指与意愿无关的事件或者自然人、法人的不以追求某种法律效果为意愿的行为;[20]法律行为则是人们以其意愿追求形成某种法律效果的行为。[21]借用“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的概念区分,我们对调解中的信息予以划分。首先申明,这种划分必须限定在调解程序这个框架内,因为我们界定的调解中的“事实”信息其实在调解程序之外也是人的意愿行为追求的结果,只是意愿发生在调解程序之外。因此,我们对调解信息中的“事实”和“行为”的区分以调解程序中人们是否以意愿追求法律效果的标准为基础。
调解“事实”信息形成于调解程序之外,它的形成不归因于调解程序;也就是说,在没有启动调解程序的情况下,这些信息就自然地在正常的诉讼程序中或通过证据展示或提供证据予以披露。相反,调解“行为”信息的形成归因于调解程序,主要基于人们对调解的信任,他们试图以自己的意愿追求某种法律效果,如果在没有启动调解程序的情况下,这些信息将不会产生,也就不可能在诉讼中被提出。因此,禁止调解“行为”信息的披露实质上就是给予调解安定性的保障;当调解程序以失败而告终时,我们应当试图将纠纷处理回复到调解程序启动前的状态。这些调解“行为”信息已经在国际调解规则中得到列举。结合司法调解的特征,我们认为其中属于高级保密范畴的调解“行为”信息包括:当事人提交的关于纠纷解决的观点和建议;当事人在调解程序中做出的承认和陈述;调解员提出的方案或陈述的观点;当事人对调解员或对方提出方案的接受或者拒绝的行为;专门为调解产生的文件。
调解保密原则将被所有参与调解的人员遵守,包括法官、调解员、当事人及其代理人、鉴定人员、其他参与调解的人员。在调解程序的开始或者邀请其他人员参与调解的开始,法官或调解员都应当告知参与人员遵守保密的义务。或者,为了强调遵守保密义务,我们建议借鉴国际调解经验,所有参与人都被要求签署一项保密声明或协议,声明和协议中详细记载有关保密的权利和义务,甚至违反的后果。例如,有关人员将受到行业纪律的制裁;泄密者因为其行为造成损失,将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法官对调解信息的保密义务。一方面,在调审分离状态下调解程序向审判程序的过渡中,调解员提交的材料以不涉及调解程序的实质内容为原则,调解“行为”信息一律不得传递给审判法官;而审判法官也无权要求调解员提交这些材料。另一方面,在调审合一状态下,法官不得依据其在调解程序中知悉的“行为”信息作为判决的依据,否则,当事人将有权提出再审之诉,要求撤销判决。 [page]
自愿原则决定保密原则的适用。当事人可以在保密声明或协议中协商约定保密原则适用的范围:他们可以对于应当属于“保密”范畴的信息授予披露的权利,或将不属于保密范畴的信息纳入保密范畴(当然,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或对程序中的信息的保存方式予以约定(例如,提出返还提交的文件,要求法院不得留副本或销毁有关的文件),或约定免除调解员遵守保密义务的相关限制等。
(二)调解的对等性
调解中的对等原则是对审原则(或辩论原则)在诉讼外领域的延伸。对审或辩论原则是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近年来民事诉讼改革力图矫正此项原则的“伪者”地位:[22]对于对审或辩论原则的阐述不仅仅限于“辩论”这个行为;关于审前准备程序中证据展示制度的构建,[23]保障当事人充分的辩论准备时间和信息掌握的对等性,以避免由于信息的不对等性而造成的辩论的空虚化。2007年10月28日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于再审事由的详细界定,包括“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这无疑是对审或辩论原则进一步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24]我国关于对审或辩论原则的构建,主要来源于大陆法系国家论述的启发。而在今天的大陆法系国家中,这一原则已经不再局限于民事诉讼领域,而渗透刑事诉讼、行政诉讼领域、甚至诉讼以外的领域,如仲裁、合同、商事、行政程序,自然也包括调解。[25]适用范围的扩张也改变了对审或辩论原则在诉讼中的严格意义。在非诉讼领域中,由于裁判第三人的缺失.两方的行为是实现信息的互动沟通,在平等了解的基础上充分讨论以达成一个明智而清楚的结果。扩展之后的对审或辩论原则,我们建议归纳为“对等”原则;此原则包含两个基本点,即保障信息知悉权和对等讨论权的充分实现。
对等原则的实现依赖于另一个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诚信原则最先出现于民法领域。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合同法》第6条规定:“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信原则意味着当事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不仅不应当欺骗对方,而且应当保持一种诚意合作的态度,及时提供有关信息和帮助,尽量协助对方共同完成合同行为。[26]近年来诚信原则适用范围得到扩张,例如,我们讨论其是否应当确立为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诚信原则在西方国家民事诉讼中的出现契合诉讼模式的转换,法官在诉讼中权力的扩张依赖于诚信原则的引导。国内有学者认为诚信原则的引入意味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此举正与当前诉讼模式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换的逻辑相冲突。[27]实际上,诚信原则的约束不仅仅针对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而且针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范使用。诉讼是自由平等竞技的过程,而不能投机取巧。程序的设置是为了保障双方自由而平等的交流和讨论的机会,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正是监督这个目的的实现。从职权主义到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完全取消法官的能动地位,诚信原则的引入也是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力行使的“新向导”。诚信原则是道德标准成功向法律领域渗透的一个体现。以往调解注重道德理念的劝说,调解员权威的形成依赖于与当事人对当地道德风俗的认同;现代调解早已脱离原有的道德圈子,缺失了调解员的道德权威和当事人之间道德观念的认同,调解的成功需要寻求新的基点。调解是双方合意的结果,这种合意必须是真实的,否则“伪合意”的结果不是消除矛盾,而是激化矛盾。同时,调解程序的灵活性使得控制调解中的交流行为难以严格,因此期盼诚信原则的运用提供一个向导,鼓励当事人真诚、自愿地进行协商、达成协议。
[page]
“对等”的调解是结合对等原则和诚信原则,诚实实现当事人的信息知悉权和对等讨论权。对等调解的实现一方面依赖于当事人之间的诚实交流和对话,另一方面期待于法官和调解员对当事人相互行为的监督以及本身对对等原则的诚实遵守。调解中虽然没有证据展示制度,但是当事人仍然可能被要求提供某些资料和声明。比如,调解刚开始,当事人可能被要求提交一份简单的关于争议的基本内容和争点的陈述;或者,可能需要提交更详细的关于理由、事实和法律根据,有关的优势证据的资料;之后,可能随时被要求提供相关的补充材料。这些材料提交之后将转发给另一方当事人一份副本;不过,如果材料提供方提出对对方当事人保密的特殊要求,则应当准许。这些材料的交换可能被确定在一个固定的场所当面进行,称之为“调解前会议”。在会议上,调解员主持下列工作:整理调解中需待解决的争点,信息的披露内容,资料的交换,专家报告的交换,调解日程的安排。
调解日程的确立不是完全固定调解程序,使之灵活性消失,日程是随时可能被调整和修改的,调解日程只是提供当事人对话和信息交流的一个指导。当然,因为日程的确立是双方当事人合意的结果,所以在之后的程序中,当事人应当遵守,而日程的修改只能通过当事人的再次合意进行。如果一方不遵守日程,另一方有权要求对方承担约定的责任。依靠调解日程,调解信息交流的对等性和时间的控制将得到保障。一览调解日程中的事项,当事人对自己和对方应当实现的行为将获得清晰了解,如果发现不对等的处理,可及时提出异议。同时,调解日程详细确立有关义务履行的具体时间。当一方没有按时完成,另一方可以拒绝随后义务的履行,甚至立即终止调解程序,如此可以有效防止某些意图拖延程序的不诚信行为。不过,不遵守调解日程不会带来严重的制裁后果,例如行为的无效性,只能导致调解程序的终止。
仲裁程序中对于仲裁员的申请回避权在实践中经常被当事人滥用,以达到拖延仲裁程序的结果。[28]这种现象在调解程序中同样难以避免。相比仲裁程序的处理,调解程序的处理将比较宽松。首先,我们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接受当事人的回避申请,撤换调解员,因为调解员的权威依赖于双方当事人的信任,他的行为能否成功同样寄托于当事人的信任。一旦一方当事人对调解员的资格和权威存在怀疑,那么调解员不再胜任调解的使命。不过,为了惩罚相关的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我们可以对回避申请提出的情形分别处理。在挑选调解员时,当事人可提出无理由的回避申请,然而,在调解员选定后,当事人的回避申请须附加理由。如果理由被证明是正当的,那么当事人的行为不构成对诚信原则的违背;相反,如果理由没有得到证实,当事人的回避申请虽然会被接受,但是其行为因为违背诚信原则,将承担有关的后果,比如单独承担调解费用。
因为调解对等原则和诚信原则的不遵守难以带来严重的制裁后果,所以控制手段主要局限在行为的预防阶段。而在这阶段,调解员的作用对于对等调解的实现非常关键。调解员必须履行其监督职能。一旦发现违反行为的萌芽,调解员立即对行为一方提出警告,提醒其马上停止这些行为。如果行为一方不听劝阻、执意进行,调解员应当及时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另一方当事人在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可以做出选择:或者忽略行为一方的违反行为,继续进行调解;或者终止调解程序。然而,如果继续调解可能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调解员应当主动终止调解程序,将纠纷转入审判程序。
二、法官在司法调解中的角色重整
我国的民事程序构造模式正在发生改变,原有的“调审合一”模式逐渐被“调审相对分离”的模式代替。[29]司法调解原有的主持人结构发生变化:在以往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或调解型审判方式中,审判法官即司法调解的唯一主持人,而今,审判法官不再是唯一的,司法调解主持人的类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司法调解的新主持人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法院内部除审判法官以外的人员,比如设置专门的庭前调解法官或由法官助理承担;[30]第二种是法院系统外部的人员,即最高人民法院在《规定》中提出的调解组织适度社会化[31]——“请进来”和“托出去”的体现。“请进来”是指人民法院依法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这种方式其实是一种传统的方式,是“依靠群众”路线贯彻的体现。[32]这些被邀请的人群通常为当事人亲属、所在单位、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信教地区的宗教界人士、社会名流、社区贤达人士、家族长辈等。这种邀请协助调解的方式与中国传统的“教谕式调解”特征息息相关,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由第三人按照法官的意图,运用情感、权威等力量向当事人施加影响,改变其态度,调解效果可能更佳”。[33]我们不排斥这种传统方式的继续采用。但是,考虑到“请进来”方式与保密原则构成抵触,我们建议,在法院决定采取这种方式之前应当获得当事人的同意,而不再是依职权单方面决定即可。在当事人同意之后,法院应当告知有关被邀请协助的人员保密的义务,不得泄露所知悉的调解信息,否则可能承担泄密的责任。“托出去”是一种全新的方式,是指在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后,人民法院委托有法律知识、相关工作经验或者与案件所涉问题有专门知识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确认,与法官主持调解产生相同的效果。这种新方式的推行尚停留于法院改革实践的个别经验,例如,北京市朝阳区法院2005年5月底颁布的《特邀调解员工作规定(试行)》。[34]从特邀调解员的组成上,大多是法庭辖区内街、乡的居委会或村委会干部,司法所所长及司法助理员、乡级领导。朝阳区法院的实践表明,特邀调解员在承担调解的工作中体现出对法官的强烈的依赖性。根据《特邀调解员工作规定(试行)》(第8条),特邀调解员应自觉遵守人民法院的各项规章制度,认真履行工作职责;配合案件承办法官审查诉讼资料,明确争议焦点,确定调解方案;协助案件承办法官进行庭前调解及诉中调解;接受法院委托独立进行庭外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经法院确认;就调解中发现或发生的事实或情况,及时与案件承办法官沟通,确定新的]二作方案。事实上,在大调解格局的组建下,人民调解网络的改善、法律服务所和司法所的改革可以提供给司法调解中受托主持庭外调解的新主持人充足的候选人:人民调解员、两所的法律T作者、司法助理。同时,依赖人民调解网络,我们还可以吸纳更多的候选人。因此,建立法院和人民调解组织之间的联系是完善“托出去”方式的最佳途径。 [page]
司法调解主体多元化的呈现引起法官在司法调解中角色的重塑。特别是当调解使命托付给法院之外的主持人承担时,法官脱离于调解员的角色;但是,法官并不因此完全脱离于调解程序之外,他将承担新的角色——调解的促使者、监督者和审核者。
首先,在调解程序启动之前,法官将评断“调解可能性”的存在。只有具有调解可能的案件,法官才决定是否启动调解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调解程序的启动得到一定程度的规制。民事案件被划分为三类案件:必须调解的、有调解可能的、不应当调解的。对于下列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除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不能调解或者显然没有调解必要的之外,法官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而对于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法官不应启动调解程序。只有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应当调解。关于“调解可能性”,有学者归纳其为各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求同存异”的共同意愿,利益冲突并非激烈的客观基础、较为明确的法律关系和基本清楚的案件事实,以及不为法律、法规所强制性禁止的合意处分之可能性。[35]不过,调解可能性的判断更多地属于一个经验问题,需要法官积累经验之后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来予以判断。[36]即使法官确认了调解可能性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调解程序的必然启动,因为有另外一个必要条件,即当事人的同意。只有在征得当事人同意之后,案件才能进入调解程序。
其次,在调解程序进程中,法官应当留予庭外调解员单独的空间。在当事人合意选择托付给庭外调解员主持调解时,自愿原则的约束使得法官应当尊重调解员的工作。法官不得任意干涉调解的实质性工作。同时,保密原则的约束使得调解员不得任意向法官披露其知悉的调解信息。可以预见的是,调解员可能因为自己法律知识的欠缺,期望获得法官的某些法律意见。在这种情形下,调解员应当事先询问当事人的意见是否同意向法官提出法律咨询。在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调解员制作一份文件,在避免透露有关保密信息的条件下,书面询问法官的法律意见。当事人有权查阅这份文件,对其中涉及的披露保密信息的行为,及时提出质疑和异议。
最后,在调解程序结束之后,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情形下,法官将负责对调解协议内容的审核。法官在审核过程中,应当避免控制标准的严苛性而重现以往调解合法和真实原则作用下以恣意改变当事人合意的现象。《规定》第12条对调解协议无效事由的规定明确界定了法官审核的标准。因此,只有当调解协议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案外人利益,或者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时,调解协议才被确定为无效。而其中“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即调解中当事人合意的瑕疵,我们认为,在调解原则重构的基础上,借助调解契约本质决定的与合同无效事由的接近性,[37]法官的审核将有据可循,有准可依。
当事人如果主张调解合意存在瑕疵,应当证明三个因素的共同存在:对方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等非法行为;这些行为与自己意愿瑕疵之间具有直接且决定性的因果关系;意愿的瑕疵给自己造成损害。损害因素的存在是因为调解程序通常具备第三人,即主持人的引导,避免了单纯合同领域两方盲目角逐的场面。在考虑非法行为与合意瑕疵的因果联系时,当事人双方的条件将被纳入判断的范围。如果双方力量明显不对等,即一方有律师代理,而另一方没有,法官审核的标准将比较宽泛;也就是说,这些非法行为即使显示不是很严重,但也可能被断定与合意瑕疵的产生具有直接且决定的联系。相反,如果双方力量平等,都有律师的代理,那么法官审核的标准将比较严格,只有当行为的违反程度非常严重的情形下,才可能判定行为与合意瑕疵之间的因果关系。 [page]
当事人可能主张调解合意的瑕疵源于调解程序中的瑕疵,即对保密、对等或诚信原则之下某些程序的违背。我们认为,简单的违反程序的行为不会导致调解协议的无效;只有程序瑕疵与合意瑕疵存在直接且决定的联系的情形下,调解协议才能被认定为无效。例如,调解程序不同于诉讼程序,强调双方当事人的对面辩论;有时,针对双方敌对情绪强烈,调解员可能采取缓冲的手段,即“背靠背”的方法,单独与当事人会面。先通过单独见面的机会了解当事人心里的症结和对纠纷处理的真实想法;此后调解员来往于当事人之间,穿针引线,实现当事人之间的沟通。“背靠背”方法的使用必须注意不得抵触对等原则。调解员应当给予双方当事人对等的单独见面的机会。调解员应当在每次单独会见一方当事人前,告知另一方当事人关于会见的事实和相关的权利,即可以要求与调解员单独会见的对等机会;对于另一方当事人的要求,调解员不得拒绝。可能在告知和询问之后,另一方当事人当时并不要求对等的会见机会。为了避免事后当事人以单独见面机会的不对等提出调解协议无效的事由抗辩,建议调解员应当在告知和询问当事人时书面记载询问当事人和回复的事实。这样,书面记载在之后可能的调解协议无效抗议程序中作为相反证据被提出。而如果在缺乏书面记载的情形下,则由法官来具体判断程序上的瑕疵是否导致了调解合意的实质性瑕疵。而对于当事人证明法官或调解员存在贪污受贿等非法行为的情形下,只要这些行为被证明确实存在,调解协议一律归为无效。
三、结语
司法调解契约化的发展取决于司法独立和程序公正的实现,因为在调解等替代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最根本的保障机制是当事人随时可终止和进人审判程序的权利。当事人发现在替代纠纷解决途径中的妥协超出自己的底线和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可以随时终止参与的行为而将纠纷转入审判程序,等待法官的公正判决。而司法的不独立和审判程序的不公正将使得人们对调解等替代途径的求助和其中的妥协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这表面看来是一种自愿的体现,但事实上是无奈之下的“伪自愿”,这正是非正义的体现。因此,司法改革、诉讼改革和调解改革必须同时进行,而前两者的成功显然决定着后者的成功。
【作者简介】
周建华,法国蒙比利埃第一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1]参见张卫平:《转换的逻辑——民事诉讼体制转型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88~314页。
[2]同上,第296页。
[3]同上,第298页。
[4]张卫平先生在其著作中论述到了应当以“诉讼和解”置换“诉讼调解”制度(同上,第313页)。这种替代的方案得到了学者们的赞同。例如,蔡虹:“大陆法院调解与香港诉讼和解之比较——关于完善合意解决纠纷诉讼机制的思考”,《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江伟:《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8~449页;李浩:“关于建立诉讼上和解制度的探讨”,《清华法律评论》(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覃兆平:“诉讼和解——法院调解制度完善之对策”,《法学》1998年第8期;张晋红:“法院调解的立法价值探究”,《法学研究》1998年第5期;章武生:《民事简易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页。然而,我们认为这种字词上的更替会与长期以来关于“调解”和“和解”的区别使用相冲突。实际上,学者们主张的“诉讼和解”的内容与其他学者主张的改革调解的内容是相同的,即强化当事人的合意。因此,我们主张更多的是对于调解制度内容上的革新。
[5]参见L.Cadiet,Les jeux du contrat et du proces:esquisse,in Philosophie du droit et droit economique.Mélanges offert a Gerard FARJET,Frison—Roche,1999,p.26 et s,spec.p.31。 [page]
[6]参见L.Cadiet,L’économie des conventions relatives a la solution des litiges,in B.DEFFAINS(dir.).L’analyse economique du droit dans le pays de droit civil,ed.Cujas,2000,p.313 et s.,spec.p.313;G.CORNU et J.FOYER,Procedure civile,PUF,3e ed,1996,p.41。
[7]L.Cadiet,Une justice contractuelle,l’autre,in Melange Jacques GHESTIN,LGDJ,Montehrestion,2001,p.177 et s.
[8]范愉:“简论马锡五审判方式——一种民事诉讼模式的形成及其历史命运”,《清华法律评论》(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新传统”,载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页。
[9]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10]参见李浩:“论法院调解中程序法与实体法约束的双重软化——兼析民事诉讼中偏重调解与严肃执法的矛盾”,《法学评论》1996年第4期。
[11]参见《民事诉讼法》第9条、第85条。
[12]参见黄宗智:“中国法庭调解的过去和现在”,《清华法学》(第10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13]参见范愉:“法院调解制度的实证性分析”,载王亚新等著:《法律程序运作的实证分析》,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236页。
[14]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6条。
[15]参见杨润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司法解释的司法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16]王怀安:《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84页。
[17]《规定》第13条针对当事人在调解书送达前的滥用反悔权的现象,将调解协议生效的时间提前,定义在“协议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应当记入笔录或者将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之后,当事人请求制作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送交当事人;但是当事人拒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可以持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18]See WIPO(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Mediation Rules,2002:UNCITRAL(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Conciliation Rules,1980: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ciliation,2002;CMAP(Center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in Paris)Mediation Rules,2006;Mediation Rules of British Columbia Mediator Roster Society,2000;Mediation and Conciliation Rules of lAMA(Institute of Arbitrators&Mediators Australia),2001;CAMCA(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enter for the Americas)Mediation Rules.1996:Conciliation Rules of CCPIT/CCOIC(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China Chamber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2005;Rules of Procedure for Conciliation Proceedings(Conciliation Rules)of ICSID(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Rules of Mediation Procedure of DIA(Danish Institute of Arbitration).2006:National Arbitration Forum Mediation Rules(USA),2006;Mediation Rules of CAS(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1999;Mediation Rules of HKIAC(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1999:Mediation Rules of CNIAM(the Chamber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of Milan),2005;Mediation Rules of SCC Institute f the Institute of the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1999;National Mediation Rules,ADR Institute of Canada.Inc./L’Institut d’Arbitrage et de Mediation du Canada In,2005;Model Code of Conduct For Mediators,ADR Institute of Canada.Inc.2005. [page]
[19]例如,《法国民事诉讼法》第131—14、832—9条。相关判例:TGI Paris,18 janv.1999(SNECMA c/Ségui,es qual.et autre),D.1999.inf.rap,p.102;A.LACABARATS,note de I’ordonnance 1e president de la cour d’appel de Paris,24 sept.1999,Gaz.Pal,janv.—fev,2000,p.121;cA.Paris(4e ch,sect.A),20 mars 2002,Gaz.Pal,mars—avril,2003,juris,p.1263.obs.LE TARNEC。
[20]例如,由于地震使房屋倒塌并由此导致租赁合同的解除;出生形成父母与婴儿之间的法律关系;死亡导致死者遗产的转移。
[21]法律行为可以是单方面的,比如遗嘱;也可是双方面的,比如合同。
[22]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23]这应当归功于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24]当然,真实意义上的对审或辩论原则,即“约束性辩论原则”(参见前注[22],张卫平书,第9~13页)的确立,仍需要很多改革。
[25]以法国为例。2001年第516号法律,将对审原则插入《刑事诉讼法》的第1条。刑事法官只能根据辩论中经过对等讨论的证据作出裁判(《刑事诉讼法》第427条第2款、第512条、第536条)。在预审中,自由与羁押法官在决定对某人实行羁押的情形下,他必须告知可能被羁押的对象有权申请给予准备陈述的时间:羁押的决定必须是在对等辩论之后的结果(《刑事诉讼法》第145条第4款)。此原则在刑罚执行中也应当得到遵守(《刑事诉讼法》第712—1条及以下条款)。对审原则在行政诉讼领域的确立更多归功于最高行政法院(le Conseil d’Etat)的判例确立,因为在立法中虽然确立预审程序或审前准备程序的对审原则,但预留太多的空间以适应紧急状态的处理。在仲裁中,由于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1460条规定民诉中的有关原则适用于国内仲裁程序,其中包括对审原则;对于这些原则的适用,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来排除。对于涉外仲裁,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1502条也能推定对审原则的适用。对审这个词出现在诉讼之外的更广泛的领域,比如社会法、民法、商法领域。在这些领域,由于缺失第三人的裁判地位,对等讨论的行为只出现在两方之间,所以中文“对审”的翻译不太适合,我们改用“对等”的词语来代替。在行政程序中,行政机关同样必须给予行政相对人一个对等讨论的机会,这是行政裁定形成程序的必要环节。
[26]参见《合同法》第60、92、119、125条。
[27]参见黄娟:“对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冷思考”,《法商研究》2001年第6期。
[28]为了遏制这种恶意轻率的行为,法国有关的仲裁判例中认定当事人的迟延异议为一种对申请回避权的默认放弃,从而仲裁员已经获得正当的仲裁资格。我国立法中并没有对此行为做出相关的规定。不过,《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21条第7项规定:“当事人在获知仲裁庭组成情况后聘请的代理人与仲裁员形成应予回避情形的,视为该当事人放弃就此申请回避的权利,但另一方当事人就此申请回避的权利不受影响。因此导致仲裁程序拖延的,造成回避情形的当事人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
[29]参见前注[15],杨润时书,第21~24页。
[30]同上,第257—279页。
[31]参见前注[15],杨润时书,第13页。
[32]参见《民事诉讼法(试行)》第99条,《民事诉讼法》第87条。
[33]何鸣:《人民法院调解理论与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34]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庭外和解促和谐,机制创新谋发展”,《人民司法》2006年第4期。
[35]参见赵钢、王杏飞:“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新发展——对《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初步解读”,《法学评论》2005年第6期。 [page]
[3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人民法院对适合调解结案的民事案件,应当调解并重点做好以下案件的调解工作:涉及群体利益,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配合的案件;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集团诉讼案件;案情复杂,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且双方都难以形成证据优势的案件;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在适用法律方面有一定困难的案件;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程度大的案件;申诉复查案件和再审案件。
[37]参见《合同法》第5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72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