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数:6 更新时间:2024-07-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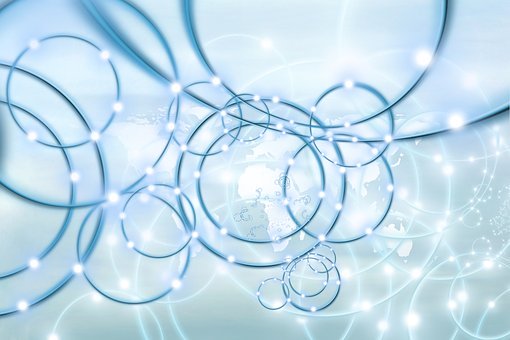
环境权作为环境法理论的基础和核心,其定位不同必然导致环境法理论的发展方向完全不同。自从1982年蔡*秋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环境权初探》以来,环境权的专题理论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相关论文在法学和环境类学术杂志上的发表已经达到数百篇。学者们从不同的环境权定位出发,得出了许多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理论观点。尽管这种百家争鸣的现象也许是一种好现象,但对于全球特别是我国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来说,我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因此,目前理论界众说纷纭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混乱和有害的无序状态,其根源在于对环境权的定位问题。
环境权仍然是一个模糊的理论术语。这种模糊性首先体现在对环境概念的理解上。目前学界最激烈争论的是环境权究竟是一种环境的权利还是人类的环境权利。对环境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其他生物和自然界都只是人类道德关怀之外的工具。而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不仅人类具有内在价值,动物、植物、物种乃至自然本身都具有内在价值,它们是道德共同体的组成部分。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应纳入伦理调整范围,人类的伦理规范应扩展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蔡*秋先生主张环境法不仅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观点拓宽了环境法的调整对象范围,符合环境法的内在逻辑和可持续发展要求。但是,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观在法律中是行不通的。传统法律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始终以人类为中心,未将权利赋予非人类生物。我们无法通过某一具体部门法改变整个社会的权利结构。任何一种权利都是某种社会权利结构的具体反映。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应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将非人类生物视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相反,这种立场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观在环境保护的根本目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上与国际环境保护运动主流观点不同,导致了公众认识的混乱。这也是目前环境权理论混乱的原因之一。国外一些环境法赋予非人类生物权利的做法并非真的改变了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实质上是为了维护人类整体利益而将非人类生物视为形式主体对待,非人类生物的权利仍由人类行使。将非人类生物作为客体或形式主体的做法并无本质差异,只是立法技术不同。因此,不能从这些立法中得出自然体享有权利的结论,更不能将这种主观结论等同于法律的真实。实际上,主张自然权利的学者故意夸大了这一观点以矫枉过正。
总之,环境权的定位问题对环境法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混乱局面。尽管环境权的定位问题存在争议,但我们应该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同时扩展环境法的调整对象范围,以更好地维护人类利益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