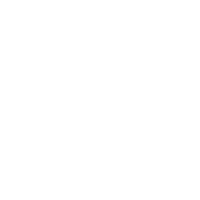
点击数:36 更新时间:2024-11-21

辩护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适用的首要原则是“无罪推定”。为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有确切和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具备适当的主体资格要求、有主观过错,实施了相关的行为并且其行为侵犯了相应的客体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而要得到这些证据必须依照法定程序、采取合法的方式取得;在认定这些证据时,要求必须是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绝对可信赖的;所有这些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链条,通过这一证据链条能够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这一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没有其他任何可能存在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在运用证据上产生怀疑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认定;如果在认定事实上产生歧义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作出解释;如果在适用法律上产生困难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进行选择。
基于上述认识,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运用证据上存在严重问题,具体阐述如下:
判决书中认定“2001年5月5日,一个叫陈胖子的人(另案处理)给被告人xx打电话称xx有文物出售,让周来xx。5月6日被告人xx到xx后打电话让被告人xx来xx购买文物,未能得逞……”的表述过于主观。事实上是xx约xx到xx看了一个花瓶,因该花瓶系仿制品而非古董,所以xx没要。这一点在庭审中xx和xx的一致供述可以证实。这里需要说明的是,xx本身就是经营古玩店的,他买卖古董(包括文物)赚钱无可厚非,只要他所收购的不是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那么就是合法行为。而一审判决书中将xx的经营行为表述为“未能得逞”,显然是在主观上已假定xx是要进行非法的倒卖活动,并且这一主观心态直接影响到对xx其他行为的认定,致使在审理查明的事实中出现偏颇。
判决书认定“……看完文物后在xxx商定47万元成交,两天后交易……”没有确切证据能够证明。可以说明这一情节的有2001年6月16日xx讯问笔录;2001年5月11日xx讯问笔录;2001年6月16日xx讯问笔录;2001年6月16日xx讯问笔录。但这些供述不能确定无疑的说明商定价格的事实存在。xx是听xx说的,xx说谈价格时只有xx和xx二人,也就是说他和xx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谈的,而xx在笔录中供述说“谈好47万”,但在庭审中又说“谈了半天没谈成”,显然上述本份讯问笔录存在诸多疑点,不能确切地证明商定价格这一事实存在。同时xx当庭供述“47万是xx定的”,这就可以说明价格问题只是单方的要求,不是买卖双方商定。,没有商定价格,当然不可能有交易,所以“两天后交易”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而xx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在只看到两件文物、还不能确定是否属于国家禁止经营的种类,也不知道其他文物什么成色、价值多少的情况下就与中间人而不是卖主商定价格显然不符合经商的常理,所以也是不可能的。
判决书认定“……当晚,被告人xx在去西安的路上给在广州的被告人xx打电话,让苏带钱来临汾购买文物。随即被告人xx打电话给被告人xx让车带50万元一同到山西临汾来购买文物……“的事实虽然存在,但不能就此说xx的行为属于犯罪行为。xx是一个古董商人,他所经营的古董(包括文物)只要不是国家禁止经营的,就不属于违法,更谈不上犯罪。xx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向朋友借钱并让朋友带钱来购买文物并不一定就是要购买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在这里,并没有确切证据能够唯一地证明xx是要购买本案所涉文物,所以不能说xx让朋友带钱来临汾购买文物的行为是犯罪行为。
判决书认定“……当日下午夏、周、贾、郭在xx尧都区平阳宾馆213房间商定交货时间时被抓获……“也不能认定xx的行为属于犯罪行为。众所周知,山西是文物大省,临汾地区更是中国辉煌灿烂的古文明的承载地。xx作为古董商人,来此收购文物是情理中事。在前次交易未或者不能交易的情况下二次来此,继续想着其他文物能否交易也是情理中事,不能就此认定xx就是要买xx手中的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也不能将xx与周、贾、郭再次接触的行为认定属于犯罪行为。
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诸多疑点,有的情节没有确切证据能够证明,有的情节存在其他合理解释,也就是说不能得出唯一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认定xx犯倒卖文物罪不符合刑事审判原则。
一审判决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共有十项,其中第八、九项与xx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没有实质性联系,现就其他几项进行分析:
关于鉴定结论。鉴定结论是认定文物等级的依据,是确定各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罪行轻重的重要指标,是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关于这份证据,xx在上诉状中从一个行家的眼光进行了分析,认为青铜器的鼎盛时期是商代的中后期和西周期间,大多属一级文物,而东周及春秋期间的青铜器制作流程和工艺都开始走下坡路,所以大都定为三级文物以下。xx的这批文物毛坯粗糙、工艺模糊,且都属于春秋早期,定为一级文物似嫌过高。为此,xx多次提出重新鉴定申请。这里辩护人认为在鉴定结论存在疑点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有义务委托有关部门进行重新鉴定,望二审法院予以考虑。
关于xx证言。xx系本案主要犯罪实施者,其出卖珍贵文物的主观意图明显,犯罪事实清楚,只因其是现役军人,所以才没有在本案中处理。因此其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不一定能以一个证人的身份不带任何功利性的如实陈述。同时他所陈述的情节除xx去他家看货这一事实外均系从他人口中得知,情节的真实性、确切性值得怀疑。
关于被告人xx供述。xx的供述可以证实通过xx与xx联系、一起与xx去xx家看货、一起商谈、五月九日再次与xx接触等事实,但对于商定价格、商定交易时间等关键情节均在庭审中予以否定。也就是说xx的供述并不能确切地证实xx要购买xx手中的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
关于被告人xx供述。xx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供述反复不定,难以确信。他所作的看货、定价、交易等供述均非他亲身感知,不具有确切的证明效力。他所作的“xx拉了一张单子算了67万,xx算了59万,最后定价48万……”的供述不符合“卖高买低”的交易常理,也于xx、xx的供述不相一致,所以无法以其供述认定案件事实。
关于xx供述。xx供述的事实基本存在,但这些事实并不能说明xx的行为是本案所指控的犯罪行为。xx买卖古董(包括国家不禁止经营的文物)属正当经营行为;在xx家看货也是正常经营行为;两天后回平阳宾馆再次商量交易也不能排除商量正常合法交易的可能;给xx好处费也不是违法犯罪行为。所以从xx的供述中并不能体现xx实施了本案所指控的犯罪行为。
关于xx供述。xx本人供述中对自已最不利的就是对xx说的“有多少货要多少”,而据他本人在上诉状中解释是指让xx给联系其他国家不禁止经营的文物,对这种文物有多少要多少,而不是说对xx的文物有多少要多少。这一解释合情合理,也可以说,根据xx的供述能得出不只一个合理解释,因此不能认定是要实施刑法中的倒卖文物行为。
关于xx、xx证言。前已述及,xx让二人携款来晋并不一定是要倒卖刑法第三百二十六条所指的文物。所以即使有这样的事实存在,也不能认定xx犯有本案所指控的罪行。
关于没收赃款赃物及决定。公安机关这一决定的作出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我国法律,被告人的行为未经审判机关判决确定的,依法不能认定有罪,从而其有关款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也不能确定。xx公安局尧都分局在一审判决尚未作出时就决定将有关款物定性为赃款赃物并予以没收显然于法不合。这一证据只能说明公安机关行为违法,而不能证明案件事实。
在庭审记录及各被告人的上诉状中均有公安机关逼供、诱供的记载。在这种情况下,在各被告人的当庭供述与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不一致时以何为准会产生疑问。这里辩护人认为,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实质是相互对立的两方,侦查机关有法定的权力和强制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具备逼供、诱供的条件和可能,客观环境对犯罪嫌疑人相对不利;而庭审中不仅有控辩双方,还有相对中立的裁决者,不存在逼供、诱供的环境,对被告人相对有利。基于“无罪推定”和“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审判理论,应当以庭审中供述来认定案件事实,以确保公正审判。
本案中,被告人xx只见到两件文物,而一审判决却将从xx家中搜到的十五件一级文物、二十一件一般文物都认定为拟倒卖的文物,并据以认为情节特别严重将xx处以七年徒刑。这一点显然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事审判原则。并且,就连那两件文物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xx已经决定并且着手倒卖。
辩护人认为,根据本案证据可以合理的得出至少两种结论,一是xx知道临汾有文物后就去看货,看后认为不能确定是否可以买卖(因所见的青铜器毛坯粗糙、工艺模糊,不像是珍贵文物),便想考虑后再定。于是一面给xx打电话让携款前来,同时与周、贾、郭等积极联系;一面前往西安办其他事,同时细细考虑。另一种结论是xx看过后发现是禁止买卖的,便不准备买,但仍然想从盛产文物的临汾买一些不禁止买卖的文物,于是就托xx等人继续打听,并说有多少要多少,同时让xx携款来晋准备扩充古玩店生意。对于前一种结论,辩护人认为最多只是一种犯罪预备,而对于后一种结论则纯粹是正当的经营行为。在存在几种可能的情况下,或者说在所有的证据不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的情况下,不能认定xx的行为构成犯罪。
所以,辩护人认为被告人xx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