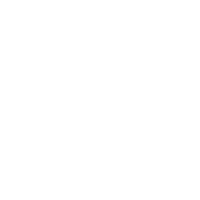
点击数:32 更新时间:2024-02-25

1997年8月1日,某县建筑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未经朱某授权情况下,(朱某为该公司会计助理),携带朱某私章,来到原告处为公司贷款,因建筑公司住所地不属于原告发放贷款的区域,故双方商定借朱某个人名义为建筑公司贷款,并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合同载明:原告贷款5万元给朱某,利率为月息11.7‰;借款期限从1997年8月1日至1998年2月1日。当天,信用社将贷款5万元以现金形式交付建筑公司。借款到期后,朱某未依约还本付息。1998年7月1日与11月20日,原告两次向朱某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经建筑公司人员劝说,朱某在二份通知书上签上名字。后原告起诉,要求朱某承担合同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明知借款实际权利义务承受者为建筑公司,同意该公司以朱某名义借款,由此产生的借款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为信用社与建筑公司,朱某在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送达回证上签名,应视为职务行为。
二审法院认为,事后朱某两次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应视为其对建筑公司无权代理行为的追认,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朱某承担。
本案中借款合同是否有效是决定朱某是否承担合同责任的关键,这涉及到我国代理法的规定。一审判决认为朱某不是合同当事人,而以合同事实上的受益者为真正合同缔约人,虽然在情理上似乎理所当然,保护了无辜的朱某,使实际上受益的建筑公司的负担其责任,较符合社会常识与民众情理。但在法律依据上却无有力之理由,其判决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法官武断地违背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脱离合同文本的约束,直取建筑公司,又无法理上有力的说明,不免有法官擅断、司法专横之嫌。将朱某在催款通知书签字的行为认定为职务行为,也过于荒唐,因为朱某签字并非以公司之名义,贯彻公司之意志,执行公司之业务,而是以个人的名义作为形式上的借款人对信用社的通知书予以签收而已。
二审判决则正与一审判决相反,严格依照法律与合同,判决朱某承担责任,此判决看似合法,但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常识上均有不妥之处。在法律上,该判决避开了信用社订约时明知的事实以及《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在常识上,此判决也显失公正,有偏袒建筑公司之嫌。因为二审法官断章取义,虽援引无权代理的条款断案,却忽略了其它相应法律关系存在和作为本人的朱某所应享有的其他救济。
本案之借款合同发生何种效力,是正确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前提。有学者认为借款合同应为无效,其理由有二,其一,合作社与建筑公司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其二,双方为规避法律行为,自当无效。
第三人与无权代理人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按我国《合同法》第52条及《民法通则》第58条、第66条,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无效,且第三人与无权代理人就本人之损害承担连带责任。所谓串通,传统民法称之为“通谋”,即双方故意的意思与表示不一致。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而为虚伪之意思表示者,谓之虚伪表示。1恶意串通,即恶意的通谋的意思表示。所谓“恶意”,民法上有两种含义,一为观念主义的恶意,指明知某种情形的存在,侧重于行为人对事实的认知,此恶意为中性的事实判断,例如,物权法上的恶意占有、合同法上的恶意第三人等等;一为意思主义的恶意,指动机不良的故意,即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侧重于行为人主观意志的伦理恶性,此恶意概念包含具有道德谴责性的价值判断,例如缔约过失行为中的恶意磋商、侵害债权的恶意第三人等等。至于恶意串通中的恶意的界定,通说认为须代理人与第三人主观上具有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故意,如果双方故意或一方缺乏故意的主观要件,则不构成串通行为。2 因此,其恶意只能为意思主义的恶意,即具有加害他人的不良动机。
在本案中,信用社与建筑公司有通谋之实,但是否以损害朱某为目的,则言之无据。究其本意,不过是以朱某为名义上借款人以规避金融部门的禁止性规定,未必有损害朱某利益的主观恶意,很难构恶意串通的主观要件。
至于该借款合同是否会因规避法律而无效?所谓规避法律,亦称脱法行为,指以迂回手段规避强行规定之行为。3我国合同法第52条也规定,以合法行为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之所以无效,是因为与合同的合法性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但我国新合同法一改以往违法性过于宽泛,合同动辄无效,当事人之意思自由得不到保障的弊端,对违法性趋于从严控制。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第52条第5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可见,违法性中的法只能严格界定为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性条款,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尚不包括其中。而本案中所规避的规范只是信用社不得跨越其所在区域贷款的禁止性规定,该规定的性质既非全国人大立法也非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充其量只不过是银行系统的行业性内部规定,对它的规避与违反,够不上违法性的标准,该借款合同并非当然无效。且从契约自由和鼓励交易的原则出发,也不应将此类合同一概认定无效。
再则,若宣告合同无效,双方返还财产,也未必能充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理顺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因为合同无效,双方发生不当得利返还之债,以恢复到合同缔约前的状态,但这一处理在法理上存在一连串的问题。
其一,朱某是否是不当得利之债关系的主体,是否担返还义务?
其二,建筑公司若向信用社返还财产,据不当得利的法理,其返还范围有善意得益人与恶意得益人之区别,在本案中,建筑公司与信用社为通谋,则建筑公司主观上算恶意抑或善意?
其三,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但本案中建筑公司使用资金的收益与风险如何分担?其多出的收益部分恢复到哪里去?若由国家收缴是否合理?
那么本案中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呢?笔者认为,首先建筑公司无权代理使合同处于效力未定的状态,而朱某嗣后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可以认定为追认行为。因为我国《民通》第66条第一款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来实施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即我国亦承认默示的追认。按一般法理与各国通例,“承认不独为明示亦得默示”,4 日德诸国判例也肯认此法理。那么朱某签字行为则是明知而不作否认表示,即默认了合同的效力,则合同由效力未定转至确定,由朱某对信用社承担偿还责任。
本案的处理结果应为根据《民通》第66条第1款,借款合同有效,由朱某对信用社承担偿还责任。此后,朱某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获得救济,一为依不当得利请求权请求建筑公司返还,较现实的做法是要求二审法院追加建筑公司为第三人,然后分别适用不当得利与合同责任处理三方关系;一为根据《民通》第66条第4款信用社与建筑公司对朱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朱某可以以此来抗辩信用社的请求权,因此最终的民事责任还是应由建筑公司来负担。
殊途同归,无论是按不当得利还是按连带责任处理,最终结果是与社会常识是一致的,即由实际的权利义务承担者建筑公司负担法律责任,问题只是法官如何适用法律规范来达到常识所应达到的目的,以实现法律正义与事实正义的统一。
就适用《民通》第六十六条而言,如进一步思考,问题还没有结束。如按《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第4款来处理,其结果就不免有啼笑皆非之处。据第66条第1款,朱某应承担代理行为之后果,而据第4款,信用社与建筑公司由对朱某的损害负连带赔偿责任。双方先后交叉请求,结果相互抵消。于是,在本人与第三人都明知的情况下的无权代理,在适用《民法通则》第66条时,将出现上述矛盾情况。法律走过曲折的弯路才符合常识的路标,常识有权利嘲笑法律的逻辑。
在本案情况下,第1款与第4款的矛盾是否能靠择一适用来避免。笔者认为,依第1款,本人承担的是合同责任,依第4款,第三人和无权代理人承担的是连带责任。此责任不可能是合同责任或缔约过失责任,只能是基于侵权的损害赔偿责任。此两种请求权之基础不同,在这种法律框架下,并存并无不可。或有人认为,第4款之情形,合同应按无效处理,可避免法律后果自相矛盾的尴尬。《民法债权》一书即认为,第4款情况可比照第3款恶意串通处理。5但此说无疑扩大了民法中法律行为无效的范围,且如上所述,恶意串通之恶意只能为意思主义之恶意,因而不符合本案事实。还有人认为,在此情况下,如本人已对无权代理行为做出追认,则认为本人已决定承担无权代理之后果,使无权代理转为有权代理,因而免除无权代理人与本人的连带责任,不能适用《民通》第六十六条第四款。但如此理解,则该条款有形同虚设之虞,恐很难有适用之余地了。因为本人对无权代理行为无非两种选择——追认或拒绝追认,若追认,则不适用该条款;若拒绝追认,则该无权代理行为转为无效,本人不受该行为拘束,实际上已从无权代理关系中脱离,剩下的只是无权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责任问题了。而无权代理行为在此条件下不可能对本人造成任何实际损害,无损害则无赔偿,故亦无适用连带责任条款的必要。
笔者认为,这种尴尬局面的出现,是由于成文法中法律条款本身的矛盾所致。《民通》的立法模式,在代理法中加入侵权法内容,以损害赔偿的形式维护代理之秩序。虽本意为对当事人利益加强保护,但带来的弊病是造成了法律体系的混乱,混淆规范意思表示的效力性规则与规范侵权行为的禁止性规则的合理区分,从而产生了紊乱、矛盾的请求权关系。代理制度属于广义的法律行为制度,其调整的行为是纯粹的表意行为。表意行为就其本身来说,只存在有效与否的问题,不存在违法侵权的问题。表意的因素只有与其他事实因素相结合,方可构成侵权行为。正如著名德国学者拉*茨教授所说,“侵权行为恒为事实行为”6,单纯的表意行为不可能造成实际损害,也就不可能发生侵权损害赔偿之债。单纯的意思表示或“法效意思根本不可能脱离其环境事实”构成违法行为,而任何违反“法律禁止者恒为特定事实行为”。这一认识甚至被奉为德国现代民法的“主要贡献”,它成为旨在区分民法中效力性规范与禁止性规范的“规范性质说”、“规范对象说”、“规范重心说”、“规范目的说”的共同理论出发点。7依此理论,即使纯粹的双方恶意通谋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意,能否对第三人产生的实际损害而构成侵权行为呢?其合意依我国法律为自始无效、当然无效、绝对无效,当然不发生其意思表示的法律效果,由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当事人可以依法定的物上请求权、不当得利等其他法律制度恢复原状即可。至于因无权代理、欺诈、胁迫而导致的合同被撤销后,有过错方所负的损害赔偿责任,其性质属特殊的缔约过失责任,其损害赔偿的范围仅以当事人的信赖利益之损失为限。即使如此,该责任也有其特定的构成要素,其中的表意因素,即受欺诈、受胁迫的法律行为应与相对的欺诈、胁迫行为区分开来,就其本身而言也只是存在效力之有无的问题。
当然,在英美法上,欺诈等行为是作为一种侵权来处理的,这一点与大陆法的缔约过失责任不同(对缔约过程中的信赖利益的保护,英美法和大陆法走了不同的道路,分别是靠扩张侵权法与合同法来实现的)。因此,按大陆法系诸国民事立法的通例,代理制度应作为一种效力性规则,仅规定一套效力要件,规定各种行为有无效力,对何人有何种拘束力即可(至多加上无权代理人对第三人的责任条款,此责任通说认为行为人恶意时当负合同责任,赔偿以履行利益为限;行为人善意时当负缔约过失责任,赔偿以信赖利益为限),其余问题悉归代理制度之外的不当得利、物上请求权、侵权行为等法律制度调整。我国《民通》之无权代理立法模式,为各国代理制度之所无,可谓极具鲜明之中国特色,但不免有法律规范适用混乱,混淆法律体系之弊,所以在适用上才出现上述尴尬,不是自相矛盾,便是无所适用。
由此,《民通》第66条第3款、第4款可不妨取消连带责任的条款或者仅规定该类无权代理之效力状态,以恢复代理制度之真面目。例如,对此类型的本人与第三人都明知时的无权代理的效力问题,在台湾民法上是由表见代理条款来解决的,如台湾民法典第169条之规定,“……(本人)或知他人表示为其代理人而不为反对之表示者,对于第三人应负授权之责任。但第三人明知其无代理权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依此模式,即维护了当事人利益衡平,又避免了请求权紊乱之弊端,其立法之简约,逻辑之清晰,处理之妥当,可资借鉴。